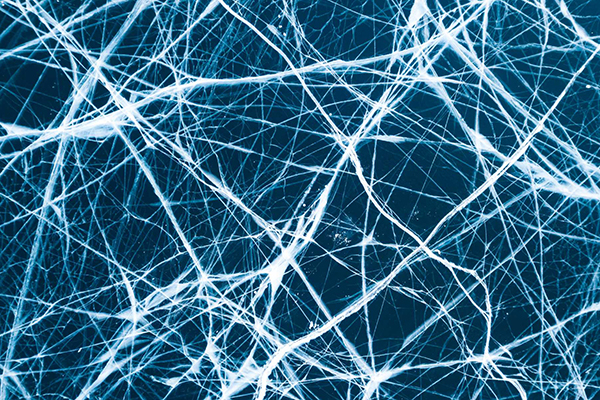《递归与偶然》一书的推进跟随着三重质问:(1)得益于哲学追求系统化思想的反思,它能否还原为一种递归性的操作?(2)如果上面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反馈(feedback)的控制论的概念是否意味着信息机器(la machine informatique)使这种类型的反思自动化,并因此实现和完成了世界理性化的哲学计划?(3)通过证明有机表征的图式(schème de représentation organique)控制着系统的观念,我们是否可以希望通过批判,借助从德国观念论一直到控制论(的思想脉络),能为哲学思想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同时面对这三个问题,于是本书不可避免地承受了论证目标致密和交错的风险,但仍然致力于精确的论证从而能使这些线索仍显得清晰可见。《递归与偶然》一书的目的在于发展出一种控制论的认识论,以便能洞察到那些有可能抵抗住信息科学显而易见的全能力量的事物。于是,上述的关键将本书的主题设置在当代关于生态学、人工智能、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e)和思辨实在论(réalisme spéculatif)的辩论中。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把作者许煜所主张的具有独创性的批判路径的争论置于政治学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本书分析的层次是思辨的(d’ordre spéculatif),但我们阅读的确实是一本充满战斗性的长篇檄文:反对西方技术普遍化的意图——并且这种西方技术的霸权目的在于使宇宙万物都听命于其计算的威力。作者发展阐明了“控制论瓦解其自身总体性和决定论思想的新视野”(278)。为此,他推进了技术本质上多样性的观念,并用以确认任何系统化都不可能是总体性的,从而捍卫自由突发(sursaut de liberté)的可能性。
我们能否在哲学传统中识别出对这个界限的超越?
于是该书的长篇导读从这个问题视角出发,对所探究的三个维度提出了质问。在前两章中,许煜展示了有机图式如何决定了哲学的系统化。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之间,康德所选择的思想通路显得十分根本:通过将对有机物的的反思融入(他的哲学)建筑术,康德明白了判断力运行的机械论概念并不足以用来思考偶然性(§10)。有机形态的多样性,使得我们有必要使用另一种基于生命目的论之上的判断(une téléologie du vivant)。许煜认为,(§14-15)正是谢林为了哲学把反思的系统性奠基于这种对自然有机的展开(le déploiement organique de la nature)之上,他才推出这一必然性的所有后果。然而作者又明确指出,这种展开是根据一种递归逻辑来解读的。在这种递归逻辑中,自然是偶然性成为必然性的系统,黑格尔以“机械有机主义(organicisme mécanique)”的形式将其激进化(103)。于是在这个意义上,谢林,但首先是黑格尔,似乎是作为自然控制论观念的“先驱”(44)。这个推论看起来或许令人震惊,但许煜予以如下证明:正是通过对莱布尼茨和谢林的解读,哥德尔(Gödel)和维纳(Wiener)才能将系统反思的总体化过程的思想数学化和计算化(通过计算机而赋予自动化)(§20-22),然后将递归性主题化为反馈(feedback),也就是说一种被执行的操作意味着对运算装置的修改。然而,这种对递归控制论的主题化介入了偶然性概念的转变之中。偶然性不再是反思必须理性化的对象,而变成了递归性运行的必要条件,它助长了系统的递归回路并促进系统的进化。于是在这个意义上,“偶然性获得了积极的意义。” (18)在理解这一点之后,许煜指出了关于系统化思维的有机图式的两个局限性:一方面,认为一个系统会是一个业已完成的有机整体的想法是荒谬的,为了继续发挥作用,它必须向外部开放并接纳偶然性;而另一方面,尽管可能的系统操作的信息自动化,但“递归性不是简单的机械重复”(4),因此在对系统性理解的方面上,机械论和活力论(vitalisme)之间的对立失去了意义。
那么,对有机图式的系统性反思的限制是否意味着哲学反思本身的限制?我们能否在哲学传统中识别出对这个界限的超越?该书在第三和第四部分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并展示了在活力论与机械论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并取名为器官学(organologie)。这与一种新的器官(organe)观念相对应,而这一新的观念许煜在对康吉莱姆(由伯格森提出)的阅读中(§25-29)得以确认。无论是生命体还是技术,器官都是生命在进化过程中找到功能形态的物质中介。在这个意义上,从器官学的角度看,物质被设想为“有组织的无机物"(173)。于是为了不援引(伯格森)生命冲力(élan vital)的假设而能够解释物质组织的生命过程,康吉莱姆塑造了一个新的规范(norme)概念:存在着这么一种以功能的规范为形式的无机环境的内化,并且反过来,也存在着一种以无机技术为形式的有机功能的外化。然而,康吉莱姆并没有注意到控制论犹如递归过程一般,允许对这种适应的活力动力学(dynamisme vital d’adaptation)进行机械论式的思考(181)。
斯蒂格勒把这种技术对象的双重性命名为pharmakon,但许煜却在其中阅读到了解释乏力的风险——它不能进一步质问在技术物中包含的偶然性的意义。
许煜随之转向了西蒙东(Simondon)的思想(§32-33)。西蒙东为了支持一种个体化的概念而批判了适应的概念,这种概念基于他所说的存在的前个体阶段的不确定性。(西蒙东的思想)开启了对偶然性的新理解,为偶然性留下了更多的空间。然而矛盾的是,西蒙顿通过控制论带来的信息概念,阐述了前个体的概念。这也是为什么西蒙东的思想之于许煜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他(西蒙东)正是通过考虑到控制论所带来的(思想)贡献,来进行哲学的改革,从而能使哲学保持着对世界理性化控制论工程的不可还原性的思考方式——控制论已经“引入了一种新的认知图式,进而引入了人类-机器关系(homme-machine)和“社会的新组织”(199),这意味着“哲学思考的新条件”(104)。事实上,一方面西蒙东在其著作中考虑到了在个体化过程中的递归性,亦即对人类而言,这些过程是心理-社会性的秩序。据此他指出,这种操作力量并不是物质性实体,而是信息,在其中首选的媒介是技术物。而另一方面,他同时也明白作为传播信息的技术界,是人类通过它来使自己个体化的。因此,试图反思自我思想个体化条件的哲学家的应该注意将焦点放置何处。西蒙东并没有发展这一思想,他将这种机器学(mécanologie)称之为一种面向带有偶然性的技术对象的哲学关注的必然。
许煜在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34-35)中寻找到了这一计划的延续,特别是在这样的思想中,即偶然性并不包含在自然的前个体化的潜在性中(la virtualité préindividuelle de la nature),而事实上,一项被采纳的为了个体而建构环境新的技术物,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能的(于是在这个意义上,斯蒂格勒把自己与西蒙东的谢林化的思想脉络区隔开来)。然而,通过这种方式极端化技术环境的重要性,它既成为个体化的条件,也成为克服这种条件的手段。斯蒂格勒把这种技术对象的双重性命名为pharmakon,但许煜却在其中阅读到了解释乏力的风险——它不能进一步质问在技术物中包含的偶然性的意义。于是,作者重拾了他在第一部作品(《论数码物的存在》)中所阐述的“第三预存”(prétention tertiaire)(§36)的概念,其目的在于思考数字技术系统的对象中所包含的人机关系的新的可能性。许煜更具体的指出,在当今这些物体不再仅仅是机械化的无机物,而是自组织的无机物(l’inorganique s’organisant)(217),即它们是自我生产自身的结构。例如,人工智能算法不仅是利用环境中的信息来发挥作用的,同样也是生产信息的(或者换句话说,包含偶然性的),以至于能够产生我们意想不到的行为、形式、和解决方案。就此,我们是否应该在这种数字技术物的生产力中期盼我们的自由?从那时起,我们明白了一个技术物在一个技术系统中发挥作用,那么所有的生产,即使是新的和意外的生产也都会被纳入这个系统中,并且只会促进其理性化能力的提高。因此,与超人类主义的观念论(这种超人类主义认为在这种增长中实现了一种“超级有机体”(superorganisme)(220),它的绝对理性将把人从有限性中解放出来。)
二十一世纪唯物主义哲学的任务
与此相悖的是,许煜致力于理解这样一种理性化——在其中事实上包含了我们的认知能力向技术自动化的全权委托,从而开启了一种应受谴责的政治全面控制的前景。因此,这也是为什么器官学——作为一种从技术体系出发而反思思想境况的哲学方式,必须首先作为一项政治计划来考虑。而从这一点来看,“二十一世纪唯物主义哲学的任务”(144)就是要让人们看到另一种偶然性的概念。最后一章致力于这项任务。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许煜重提了之前章节关于技术根基的讨论成果。在海德格尔的视野下,作者指出了将技术系统视为超组织(superorganisme)的观念论的错误,这一错误之处在于认为技术会有一个可识别的基础,仿佛技术有一个统一的原则,使技术物有可能成为一个系统。然而,正如同西蒙东所理解的那样,拷问技术的谱系是更为切题的任务。许煜此处的贡献在于,他展示出这一谱系是多重的,因为技术始终内嵌于“宇宙技术(cosmotechnique)”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技术物的使用和演化始终与道德观念以及与自然的某种关系相连接。然而,宇宙技术往往不止一种,并且许煜所捍卫的这种基础的多元主义,使得技术差异不仅位于一个系统内的创新性生产,而且介于采用这种或那种对象的宇宙技术的方式之间。在这层意义上,偶然性并不在于技术物的形式之中,而在于宇宙技术类型与技术物关系的多重性之中。然而,这种被许煜所命名的“技术多样性(technodiversité)”的多重性,从根本上说是不能被还原至技术体系,甚至是完全的系统化之中的。
宇宙技术的偶然性是绝对的、是不可计算的,它总是打开了对技术质疑的通路。作为书中的最终困难,为了澄清绝对的偶然性的观念,许煜必须发展出不可计算的概念(le concept d’incalculable)。虽然并未陷入非理性主义泥沼,但这一(概念的)问题在于,在今天这个看上去一切均可计算化的语境下提出不可计算的问题,会或多或少地又把讨论隐性地逼退回与康德的讨论之中。“在技术体系成为自组织的无机体的时代,我们如何能够解决不可确定性的问题?”(235)特别是许煜和梅亚苏(Meillassoux)(§42)之间从体系的认识论视野出发所展开的讨论。首先,许煜表明其偶然性的概念仍然是西方中心论的,因为它建立在犹太-基督的世界先于人类的观念之上,它应该被视作是一个单一的世界体系(自然)。然而,许煜并没有在系统内部思考偶然性的绝对性,他针对宇宙技术的概念作出了反思。这个概念之所以具有战略意义是因为它允许我们思考一个诸系统根基的多元主义(在其中自然、技术和道德价值共同决定)。而这意味着在人类身上找寻可以逃避系统化的东西:人,因为他可以根据不同的宇宙技术来进行个体化,是基于绝对的偶然性之上的。这种对于偶然性的思考方式来自于利奥塔称之为非人(l’inhumain)的(思想资源)。然而,这种思考只在一定程度上切中肯綮。(§41)因为,继海德格尔之后,利奥塔认为技术系统只是一种“异化的机制”(une mécanique aliénante),因而仍然是一种“否定的器官学”(une organologie négative)(253),在其中人和技术的关系的根基应要摆脱人的技术决定。然而对非人的宇宙技术的理解,可以允许对技术问题采取多元主义的进路。这意味着,技术体系的极权化野心永远无法实现其目标。在此意义上,“技术多样性总是和内在于机械论之中的总体化力量(le pouvoir de totalisation)相冲突。”(278)在这个意义上,非人的绝对偶然性意味着个体在面临技术系统的计算霸权时的不可还原性:“积极地看,非人是抗拒系统化,以及抗拒被还原为计可计算的东西。”(235)
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借助中国思想来质疑西方思想
其次,在梅亚苏那里,绝对偶然性的观念必须要找到一个科学的全新标准,即数学化。然而,符合这一标准的非康德主义的认识论,预设了知识是建立在与人类感性(非关联主义, non-corrélationnaliste)相脱离的符号(signes déconnectés)之上的。许煜指出,由于对递归概念的历史(260)及其与技术关联的忽略,这预设了一种逻辑,在其中递归性仍然保留了一种计算主义(computationnalisme)。针对这种数学主义,许煜从利奥塔那里承接了他的反思;根据这种反思,非人同样指定了在人类内部他所不是的东西(263),并由此建立起对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功能障碍的可感关系(240)。因此,许煜肯定了这种观点:这种基本的感性(§43)意味着人与机器建立关系的那种递归性,并构成了认识论的真正宇宙技术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人的非人性是“超越系统的可能性”(263)。因此,许煜进行分析的关键之处在于是发展出一种反思,这种反思将成功地建立在这种超越的基础之上——并非超越系统,而是在系统之间。尤其是许煜和李约瑟(§44)讨论了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借助中国思想来质疑西方思想(273)。
在其交流于今日要产生最坏结果的两种宇宙技术的张力之中,许煜为了达致与其所描述的问题症结相同的理论水平,他似乎传记式地构建了必要的概念手段。无论如何,他所提出的对递归理性的批判具有如此丰富的独到之处,这种批判使我们面对自身的有限性,通过拉开一段有益的思考距离,而向我们展现了一种未曾料想的自由,这些都推进了我们思考的视野。尤其是,这第三本专著在许煜工作中所显现的强有力的思想连贯性,给我们提供了得以一窥见欧陆哲学史以及其重新连接的理念:一能够也必须要能完成的任務。随着形而上学的解构,我们已经明白,在这种哲学任务的可能性也蕴含于其完成的不可能性之中。尽管如此,也许正是因为许煜让我们沿着可怖的控制论机器行进的同时,作者又让我们重新感受到了这种古老而崇高的理念,我们才感受到了一种特有的哲学思考的欢愉,而这种欢愉在今天的阅读中是非常难得的。与超验哲学被抛弃相反的是,如果超验哲学把论域涉及到思考控制论条件的转变问题的话,那么它好像仍能够在二十一世纪寻找到意义。
译 | 胡恩海
校 | 李科林
审 | 许 煜
* Recursivity and Contingency(Yuk Hui, 2019);该书中文版《递归与偶然》2020年9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图书出品。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