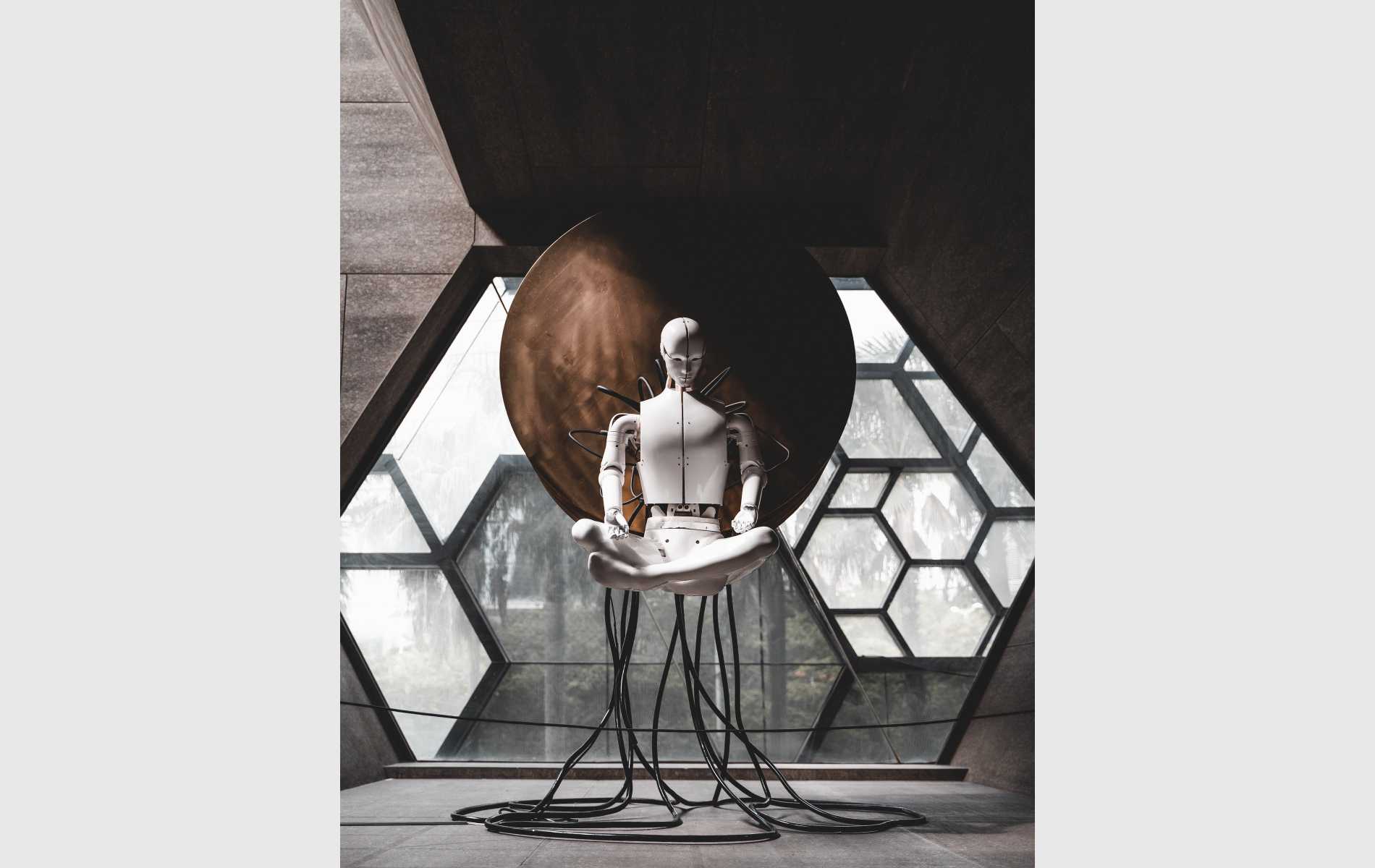人工智能是人的产物、文明的产物。它象征人类的物质文明达到某个制高点,但对人类及其文明也构成了重大的挑战。本文主要从包含在中华文明中、产生于轴心时代的中国哲学的角度来思考人工智能,但我的确并不认为中国原初精神和哲学思想能给出对现代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大概任何一个文明的思想传统都不可能为现代文明的症候提供一种灵丹妙药,但又都含有对这一危机中某种因素的解药—假如我们能认真思考古典的思想。
回到轴心时代来思考,也就是回到人类最早的精神资源、回到较早的人类来思考。“后人类时代”的概念被提出,而我们对“最后的人”的思考也最好结合对“最初的人”的思考来进行。这里的“最初的人”是指最初的文明人,尤其是最初系统深入思考的人。
中国哲学是一种强调身体及其感受性的哲学,但它并不是要去努力满足身体的各种感官欲望,而毋宁说它是要认识到人因其身体的感受性而具有脆弱性和有限性的特征,人才能追求符合人之为人的生活。
中国哲学的相关思考
传统中国哲学是基于农业文明和农业生活方式的。孟子的“为民制产”描绘了这样一幅生活图景。士人们多来自乡土,也回到乡土。下面我想说说中华精神文明的诞生时刻,即春秋战国期间的几位儒、道两家的代表人物,谈谈他们与人工智能的相关思考,也分析他们之间的一些差异。这种思考主要是围绕着天人关系、心身关系展开的。
“天”在中国哲人那里有两解:一是冥冥中的超越之“天”;二是自然之天,指整个自然界。这两者又是常常联系在一起的。人文主义的儒家和道家都不敢说知晓那超越之“天”究竟是什么。中华文化并没有发展出一个独立的、明晰的宗教体系,但这“天”是存在的,敬畏是存在的,它以“天意”“天命”“天道”在发挥着作用。无论哪一种“天”,都构成对人的作为的限制。人并没有无限的可能性、无限的可完善性。人类的历史、文明也 并没有无限的可能性。人面前并没有无数的道路可以选择,甚至 有时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人要自知其有限,最好是顺应自然、仿效自然,不破坏事物的自然过程。道家甚至希望人尽可能地回归自然、融入自然。
儒、道两家都讲顺天,顺应自然,但道家尤其是庄子还反对人伦教化乃至政治秩序。在天道方面,道家也主要取自然的收敛之道,甚至从源头上就收敛。儒家还取自然的生长之道,也讲究人伦教化,但这种人类也是“自然的”人伦—儒家最重视的是基于人伦血缘的“亲亲”关系。总之是尊重自然,没有征服自然的打算。“天人合一”即便说目的是在顺天为人,途径也还是顺天、敬天。这和现代高科技试图改变甚至颠覆事物的自然进程完全不同。
农业文明肇始的时代,人们使用的工具相当简单,常常只是身体器官的自然的、可见的延长。即便后来人类取得了很多进步,但人类对自然的改变也还是有限的。虽然种植和畜牧不再是狩猎采集现成的自然物了,各种被种植的植物和被畜养的动物的属性也会慢慢发生变异,人类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认为它们应该“择优而存”,但这种变化没有改变太多事物的自然进程。
除了外物,中国先贤也常常感受到存在于自身的“物”—肉身。中国哲学是一种强调身体及其感受性的哲学,但它并不是要去努力满足身体的各种感官欲望,而毋宁说它是要认识到人因其身体的感受性而具有脆弱性和有限性的特征,人才能追求符合人之为人的生活。作为碳基生物,人的身体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有肉身就需要物质的营养,就会产生各种欲望,除了基本的“食色”,还有更高的“权钱名”等;二是有了这种有限性,人才会渴望无限,也使基于这种有限性的德行和艺术美焕发出特别的光辉。
我们就以儒家最看重的一种德行“孝”为例。人为什么要孝敬?从身体的角度看, 一是我们和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先有一种身体或者说血缘上的联系,“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二是人刚生下来时并不能够独立生存,需要父母的抚养,孔子说三年守丧,因为父母至少要含辛茹苦哺育你三年,你才能“免于父母之怀”。即便孩子稍微能够生活自理,而后父母还要花费大量的抚养和教育时间。所以,孔子对弟子说,如果你连三年丧都不守,你觉得安心,就这样去做吧,我无法安心。三是,人都是要老的, 老人也会衰弱,进入难以自理的年龄,必须“有养”,需要儿女的照顾。而且他们不久就可能告别人世,父母年高,“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人都是要死的,不要等到“亲不在”,不能孝敬奉养才意识到这一点而后悔莫及。“慎终追远”,这种孝敬既是一种属于人的精神感情,如孔子所说,“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但又是基于身体感受性的。
中国传统的人文理性是伟大的,传统的智慧敦敦告诫我们不要随意改变事物的自然进程,不要放任物欲。
儒家对人的有限性以及多数的有限性是有充分认识的,人要受到自然的限制,受到“天命”的限制,多是来自对人的自然本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本身又是通过身体对外物的感觉和对原则的直觉,也就是通过“体知”或者说“体悟”获得的。
人的感受性也就是脆弱性。这种感受性表现为:一是人不能直接承受打击,小的打击造成人身体疼痛或残损,大的打击甚至会使人身亡。二是人必须不断摄取营养才能生存,而人最后也逃脱不了死亡。换言之,这种身体的感受性也是一种脆弱性,但正是这种脆弱性催生了政治秩序,催化了德行和艺术。这种脆弱性也帮助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文明也就建立在这种脆弱性的基础上,人类文明本身不管看起来多么强大、多么了不起,它实际上还是脆弱的。我们可以考虑特别短暂和有限的东西如何与特别长远和无限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特别肉身的东西如何与特别精神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正是因为人的脆弱性和有限性,人们才努力在家族的繁衍、艺术和宗教的创造中去追求永恒与无限。
道家也强调人有身的局限性。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有身就会有欲望,而欲望不断增长,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导致再多的东西可能也难填入的欲壑,所以,不如从源头处就加以遏制,鲁迅曾经说,“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老子希望不刺激人们的欲望产生,甚至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恍若“无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使民含德如“赤子”,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绝学弃知。庄子也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己”,不如从一开始就不去追求,恍若“无我”。道家采取了一种看起来比儒家更彻底的节制物欲的办法,当然,这种办法看起来也将遏制文明的发展。但是,具有这种身体及其有限性的根本性意识,却不无一种由“知始”而“知止”的意味。
道家想从源头上防范后果,老子并不倡导废弃政治文明,但希望人类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中去,庄子则试图使人类回到原始时代,使民“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当然,这里还是有多数和少数的分别:儒家讲圣人与众人、君子与小人的分别,但两者并不在出身上有所固定,而是保持一种上下的流动性。道家希望多数人回到人的懵懂状态、婴儿状态甚至动物状态。但其实又有极少数人(或是政治统治者,或是文化精英)不是懵懂的, 而是有意为之,(老子认为)他们背负某种精神的重负或者(庄子认为)他们获得了精神的自由。道家看来也并不是让所有人都等同于或接近于无知无识的自然物。在老子那里,统治者还是要背负判断和治理的负担;在庄子那里,除了绝大多数浑然于其他动物的人,还有极少数通达甚至拥有某种超自然能力的真人、至人。
儒、道两家思想的核心关注点都不是人类社会的不断繁荣之道、富强之道,而主要是考虑其长久之道。或者说,儒家更多的是考虑文明存续的长久之道,道家主要是考虑人类存续的长久之道。道家担心“物壮则老”。儒家是现实的,知道文明不可能倒转,文明也有文明的意义。道家是回溯的,但在精神状态上也向往一种自由逍遥的真人。儒家更重视人际关系,道家更重视人与物的关系。儒家文化中并没有多少解决今天人工智能和其他高科技可能带来的危险的现成答案,它一直关注的是人际关系和人类社会。倒是先秦道家在这方面想得较多,身处乱世,他们看到了精英对强力的崇拜,以及其背后更广泛的人们对物质的欲望。他们不像儒家那样更关注对强力的驯化,而是关注更为根本的东西,即对物质欲望的源头控制。道家对物欲有更多的压抑,或者说是从一开始就压抑—最好不产生这种物欲,不提供容易产生这种物欲的条件和环境。但两家都相当充分地认识到人的有限性,尤其是社会的有限性、多数的有限性。他们还希望在没有神灵的情况下达到少数个人的完善—前者是成为圣人,后者是成为至人。
中国传统的人文理性是伟大的,传统的智慧敦敦告诫我们不要随意改变事物的自然进程,不要放任物欲。
或许人们可以批评说,仅仅做到人文理性可能是不够的,仅仅认识到自然之“天”的限制是不够的,还要有神圣之“天”,在儒家那里也并不是没有这层含义,先人也有这种传统,但还是稀薄的一层,不是对一种超越性存在的明确认知。而这种对超越性存在的肯认也是有不同形式的。人们可能依旧不能确知这一超越性的存在究竟为何,但应该相信它一定是存在的,并努力寻找。对于超越于人的无限和永恒的寻找就意味着我们对自身的有限性有了认识。反之亦然,因为我们知道了自己的有限,才有了对无限的渴望和追求。
假如机器真能获得一种价值观,它也就可能获得一种自我意识。这时,价值观的实际指向的结果逆转只需要一个主体的转换。
人工智能与人类未来
从其起因来说,轴心时代产生的主要思想都是“忧思”。佛教的思想是因为释迦牟尼看见人的生老病死所产生的忧思;希腊思想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人看见雅典衰落所产生的忧思;犹太先知的思想是先知看见犹太人颠沛流离所产生的忧思;中国也不例外,春秋末年到战国所产生的那些最有力的思想也是我们的先人看见礼崩乐坏、战乱频繁所产生的忧思。对于如何化解这种忧思、解决所面对的问题却有了不同的路径。轴心时代产生的主要思想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都不是以满足人的欲望,尤其不是以满足人的物欲为目的的。从影响与结果来说,轴心时代的各种精神文明产生之后,此后2000年各大文明的主要关注点还是在精神,而不是在物质,是在人的精神自控和超越能力,而不是在人的控物能力。
中国古代的士人将“先天下之忧而忧”看作自己的使命。今天,我们看一些现代人的忧虑或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人类精神文化衰落的忧虑,这是在近代以来就开始的。现代人越来越多地关注物质层面生活的改善,人们忧虑精神生活是否会往上走而不是会往下走?第二阶段是对人类文明的忧虑,这在 20 世纪就开始表现得较为充分了,尤其是经过世界大战,出现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后,人们忧虑新的世界大战是否将把人类“打回石器时代”,人类近万年积累的文明成果还能否延续?第三阶段则是在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高科技出现之后,对人类这一物种可能将被取代,还能否存续的忧虑。而人类是否存续,文明是否存续,是否将取决于人类能否重建一种精神秩序,包括重建人类与一种超越性存在的精神联系或契约?
我们还是回到对人的理解和定义:人是什么?人能何为?在直接讲到人性的时候,孔子只是简单地说“性相近,习相远”,“性相近”则意味着人有一些共同或接近的本性,即便具体落实到每个人身上有些本性的差异,也还是能够概括出一些相同的因素。但不同人的作为,不同人的后天习性,不同人的“盖棺论定”,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地方尤其是不同政治社会的风习可能 是相差甚远的,这其中有不同社会的制度、组织和文化的作用与 影响。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环境影响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我们要看 到之所以存在善恶差异,还是因为在人的本性中一开始就有了善 端和恶端。这两端的差距在“人之初”那里是不明显的,但如果 没有两个始源,也就难以解释后来的善恶分流。
即便是大力主张人性本善的孟子,我们也能注意到他是在“善端”的意义上谈人性本善的,他所采用的“孺子将入于井”的例子是很基本、很低调的例证。而且,他强调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其实是“几希”,就那么一点点。“君子存之,庶人去之”,他强调人是多么容易放逸,丢失本来的善心,所以人要非常努力地求其“放心”,努力去成为一个“君子”。
而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儒家虽然意识到人有普遍的善端,但也意识到人存在一些基本的限制,人的道德能力不可能普遍上升得很高,甚至只有较少的人能够比较充分地摆脱物欲。如此也就不能指望人性自身被改造和提高到接近于圣人的程度,不能指望所有人都极大地提升自己的自控能力。如果人极大地提升自己的控物能力就可能会成为问题。
我们再回到人的定义。历史上对“人”的定义或是侧重身体及其控物能力,或是侧重精神创造与超越能力,且常常侧重人与动物之别。侧重身体及其控物能力的定义如人是直立的、脑容量大、两足无毛的动物,人是能够制造工具的动物等;侧重精神创造与超越能力的定义如人是有意识、有精神、有自我的动物,人是有价值观和正义感的动物等。我们还可以再仔细分析一下这些定义。
当我们从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本性角度说到“何以为人”的时候,大概可以包含四种特征。
第一,人是能够制造和运用工具的动物。人有理性,会计算,有逻辑和抽象能力,能够自我学习,计划自己的行动,有明确目的和手段的意识。此外,人能够利用一切可能的工具,这意味着人有控物能力。这类似于帕斯卡所说的“几何学精神”,或者说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计算理性”“工具理性”“技术理性”。
第二,人还有工具理性之外的精神能力和意识,这就像帕斯卡所说的“敏感性精神”。人还有默会的知识、情感、意志、直觉和信仰等,这意味着人有自控和超越能力,也有一种精细的、基于身体感觉的控物能力。另外,人还有直觉,这种直觉不是对外物的知觉,而是对一些抽象原则和知识的直接知觉。人还有道德感、正义感,这种感觉也不仅是为自己所生发,同样来自对他人和社会受到的不公平的反应。人是道德的动物,这并不是说人就是天生合乎道德的动物,而是说人是能够在善恶正邪这些问题上敏感、有反应的动物,是能够在这方面进行自我评价和对他人评价的动物。人在有些感知和身体能力方面(如飞行、潜水、速度、力量等)并不如某些动物,甚至人的这些能力还有退化的趋势; 但人有理性、精神和道德感,就能够建构社会政治秩序,发展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当然,人在这方面的发展也不是无限可完善的。
科技的发展也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自信。在一种自得其乐和自信自满中,人们将很难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很难会去渴望一种标识出人的有限性的超越性存在。
第三,人还有一种综合性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能够将人的各种理性和非理性能力与意识综合在一起,形成自己毕生的计划和连贯的行动,确立自己的人格。以往对人的定义主要都是将人和其他动物比较,但如果和新出现的智能机器比较,则还要加上一种特征。
第四,人是一种碳基生物。过去诸如人是两足无毛的动物、人是直立行走的动物、人是脑容量较大的动物等定义,虽然是着眼于人与动物的区别,但也都是从身体方面来定义人的。动物仅仅在这第四种特征上与人相似,动物的身体与人的身体虽然有重大差异,但人和其他动物一样,也是碳基生物。人和其他动物都有感觉,都需要不断补充物质的营养,都经受不起外力的重击。人和其他动物的身体及其特征都是千百万年自然演化的产物。
智能机器则仅仅在第一种特征与人相似,即拥有高超的计算理性、工具理性,能够自我学习、深度学习,而在这方面,它的控物能力在未来还可能超越人类。但是,智能机器目前还没有工具理性之外的意识和能力,没有综合的自我意识,也没有碳基生物的身体。
那么,未来的智能机器会不会获得上述第二种甚至第三种特征,或者说人类会不会推动这一过程,比如试图让智能机器变成一种结合第一种特征和第二种特征的“类人智能”。但第二种特征和第四种特征密切相关,智能机器大概能够做到拥有人类面容、人造皮肤,甚至拥有仿人的神经网络,但不可能也无须有与人类一样、与动物一样的碳基身体。这身体也正是人类的弱点。虽然人类的第二种特性或者说人类更高或更特别的精神意识能力正是基于这一弱点而存在的,还有一些像“庖丁解牛”那样的需要身体感觉的手工技艺也是基于此练就的,但智能机器要发展它的控物能力,看来也不太需要这类技艺。目前,人类对机器改进的方向的确也只是想提高它们的智能,而不是想让它们产生爱的能力、追求美的能力、拥有信仰的能力,且看来也几乎无法做到这些, 因为这些和漫长的自然演化产生出来的身体以及人心中不知缘何产生出来的灵性有关。而且,在人类目前还能控制和掌握智能机器的前提下,在人类完全能够轻易地自然繁殖的情况下,从人类的利用厚生的角度看,人类也没有这种让机器在身体上也完全变成人的需求,且不说有没有可能。
从人的角度看,将第一种特征和第二种特征相结合的更有可能的路径是在人的身体内不断植入硅基体:换上人造肢体、植入人造心脏等。就像库兹韦尔所希望的,人类最后也获得和机器一样的(可以不断更新器官意义上的)长生不老,即一种硅基“身体”。但如果这条路能走得通,就意味着人的物化、人的硅基化了,人类也将失去前面所说的那种基于碳基身体、基于人的有限性和中间性的精神特征与创造。
至于要回答人是否要给智能机器植入人的价值观的问题,我们可能首先要问,人类现在的主流价值观是什么?我们可以重温庄子那段著名的论述,那位不愿使用杠杆的为圃者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今天的“机事”是大大发展了的,那么人类的心灵是否也变成“机心”了呢?何谓“机心”?大概也就是便利之心、利用之心、控物之心。这种“机心”既是“机事”发展的动机,又是“机事”发展的结果,它们互相强化。现代人当然希望机器能够尽可能地方便人类,为人类造福,前提是机器能够置于人类的控制之下。但机器一旦获得自我意识,按照同样的逻辑,它不是也可以甚至应该利用和控制人类吗?
那么,问题就变成了人们其实是想把一种无论人类自己追求什么,机器都应该对人友好、忠心耿耿地为人类服务、绝不伤害人类的价值观植入机器。虽然可以说这是自私的,是一种“主人–工具”甚至“主奴”的价值观,但这也是能够被理解的。且不说这种价值观输入的可能性,它总是要冒这样的风险:假如机器真能获得一种价值观,它也就可能获得一种自我意识。这时,价值观的实际指向的结果逆转只需要一个主体的转换。
我们也许需要回到最初创造精神文明的人,回到最初那些系统地对人进行反省和思考的人来重新思考人的本性和命运,即为了避免单一方向的人为进步的终点而回到起点。
的确,如韦伯所说,经济和物质是基础,但精神信念或者说价值观是主导。物质或者说经济、科技是文明进化的基础,但价值观决定文明进化的方向。现在的问题是:物质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初始,但物质文明越过某个顶峰会不会也是人类文明的终结?世界会不会进入一个“后人类时代”,今天的人类会不会成为“最后的人”?我们人类这样一种造物,是否也让自身处在一个新物种的“造物主”的地位,从而开创这一新物种的“创世记”?像超级智能机器是否将把人类推到物质文明的顶点,但又将人类抛入深渊?
物质是基础。文明自物质始,但会不会也将自物质终? 人类的文明从物质文明的奠基开始,会不会也以冲上物质文明的顶峰结束?一般来说,人首先要吃饱饭,有剩余,也得到了对生命和财产的基本保障,其次才能从事语言文字和思想精神的创造。人类文明从物质开始,从农业开始,无论什么时候,物质生活和身体生存都是最基本、最优先的前提或者说目的。但今天的文明将物质生活和身体生存这最基本的目的变成了主要的甚至最高的目的,人类文明会不会也将在这种对物质不断增长的欲望以及均富的追求中结束自己?
的确,现在还不是物质文明的顶点,但人类似乎不可遏制地想要更多,想要冲向顶点。然而,人性并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人的道德能力并不会随着其控物能力的提升而大幅提高,于是,在人类的控物能力和自制能力之间将产生巨大的差距,越来越不相称,这将带来一种危机四伏的局面。科技发明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除了核武器,还有被更为隐蔽地储存着的或者可以随时被生产出来的化学和生物武器。而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等也随时可能给人类带来危险。但科技带来的经济上的极大发展与物质生活的充裕和舒适,则让人不仅感觉不到危险,而且在这种物质生活中自得其乐。科技的发展也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自信。在一种自得其乐和自信自满中,人们将很难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很难会去渴望一种标识出人的有限性的超越性存在。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而未来的人类会不会以一种“安乐死”的形式结束自己的人生?
或许人们会斥责这些忧虑过于悲观, 其实悲观到某一极致之后就达观了,这就是中国古代先贤所说的“ 尽人事,听天命”。而且,人也可以有另一种日常生活中的有用达观:活着,不多想,好好度过每一天。
当然,人总是有选择的意志的。假如说一个人的一生有两种选择,一是快速与短暂的辉煌,二是慢速与长久的平淡,人们会选择哪一种人生?可能会有一些人宁愿选择在短暂的生命里活得轰轰烈烈,也不愿平淡地度过长寿的一生。但选择后一种人生的人会不会更多?问题是人类的选择与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在人类历史中,只要有一些关键的少数做出了选择,大部分人可能就不得不跟着走了。
近代以来,人在控物能力方面的发展足够卓越,成就足够大,但从总体来看,人类精神文化的衰落已是事实,或者目前来看似乎已成定局,人类未来的命运则尚不知晓。高科技或许剥夺了一些这样的机会—通过并不剧烈的灾难让人类改弦易辙。但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有一些温和的期望,即我们也许可以有意识地推动一些高科技帮助我们部分地回到大地,回到对自然的清新感觉,恢复对劳动的美好感受,促进工匠工艺的发展,促进人类获得默会的知识。
人类几百万年都处在前文明的时期,相比之下,人类的文明史只有约一万年。一万年久吗?从个人生命来看是极长久的(所以总有人会期望“万岁”),而对一个物种来说,则是太短暂了。而这一万年的文明史又有约9500年都是处在农业文明时期,只有最近的500年是处在工业文明和高科技文明。与生活在一个社会动荡乃至战争动乱的时代的人们相比,生活在一个经济和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的人们是幸福的,甚至常常能感受到惊喜。即便对此感觉不那么良好的人,也还是有认识到这种巨变的幸运感,但是,这种人不免要忧虑人类的后代:后人会为这种前人的幸运付出沉重的代价吗?
正是基于上述种种考虑,我们也许需要回到最初创造精神文明的人,回到最初那些系统地对人进行反省和思考的人来重新思考人的本性和命运,即为了避免单一方向的人为进步的终点而回到起点。除了思考人类的繁荣富强之道,我们也要思考人类及其文明的长久存续之道。
摘 | 蓝天蒙
本文摘自《智能与智慧——人工智能遇见中国哲学家》(宋冰/编著,中信出版社,2020年2月);原题为“回到‘轴心时代’思考人工智能”,篇幅较长,略有删减。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