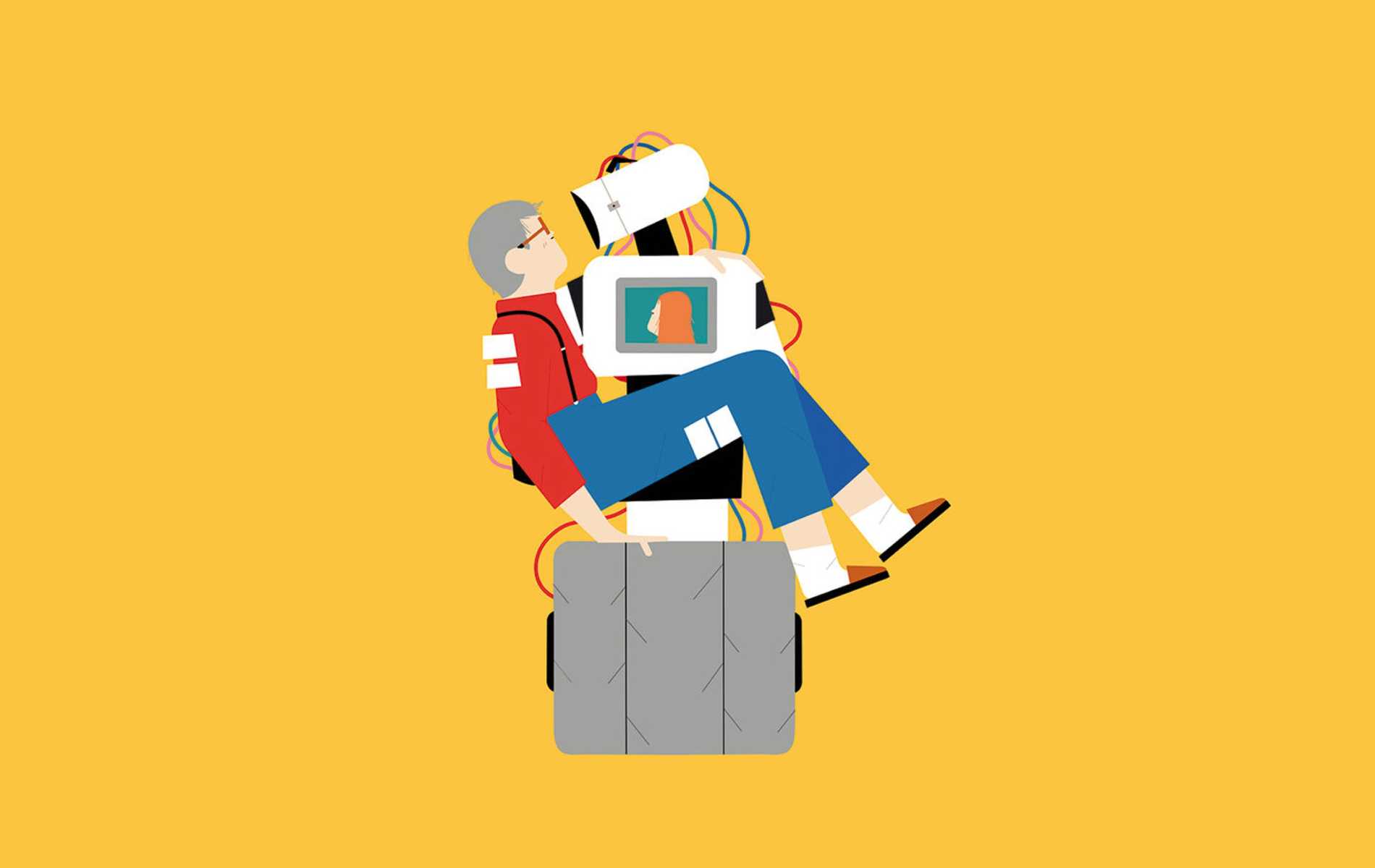Covid-19疫情让护理机器人大显身手,它们不仅承担着导诊、送餐、消毒等后勤任务,而且为医生诊疗提供数据,为隔离患者提供社交陪伴。它们的形态千差万别,功能也各不相同,要反思它们在当下和可见的未来带来的深刻伦理挑战,有必要更清晰地界定护理机器人范畴划分的基础,考察其所服务的根本目的,进而重构适合其伦理特殊性的理论框架。
对护理机器人伦理反思的出发点
护理机器人(Care Robots)是一类特殊的服务机器人,它的划分标准依据它所服务的主要目的,即保持或改进人类的健康状态,以及满足人们对于护理或者关怀(care)的需求。学界通常接受这样一个具有解释灵活性的定义:“护理机器人可以定义为在护理(或关怀)实践中使用的,用来满足任何护理(或关怀)需求的机器人,它由护理人或被护理人或者二者共同使用,被用于医院、养老院、临终关怀中心或家庭之类的场合。”[1]
护理机器人这一范畴划分遵循了世界卫生组织所倡导的健康的宽泛定义,它跨越了传统的医疗和非医疗机构的划分,强调不仅需要通过专业的治疗和康复措施来去除疾病和伤害,而且需要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得到恰当的维护。而陪护或者护理所体现的对幼儿、病人、残疾人、老人等脆弱人群的关怀,它也不止于医院、养老所、康复中心等专业机构所提供的一系列专业护理活动,同时包括所有为了满足老弱病残合理需求的实践,它是一个在包括家庭在内的不同情景中不断延续的完整进程。 [2]这种对健康和护理的整体论理解反映了当代医疗伦理学和关怀伦理学(care ethics)的基本价值取向,也应当成为我们对护理机器人进行伦理反思的出发点。
机器人成为关怀提供者的两个特征
关怀伦理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源自女性主义思想传统。它强调伦理的出发点不是独立的、自主的道德主体,而是相互关系的、相互依赖的实践活动。道德主体在具有理性的谋划能力之前,首先是一个需要他人关护的儿童,需要在教育中不断成长才能具备独立能力;同样,伦理生活也不能抛弃身体智力上存在障碍的残疾人和暂时机能受损的病人。
关怀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让我们反思伦理生活的根基位于何处。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义务论的伦理学,都预设了道德生活的立足点是根据自身资源和理性能力决定人生的理性行动者。关怀伦理学不否定人作为理性主体的自主性,但邀请我们去反思这种自主性是否是无条件的、不依赖于关系的。它主张关怀者与被关怀者之间多样而复杂的关系构成了伦理生活的起点,让我们意识到过往的伦理反思存在缺陷和偏见。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女性和儿童都不是有能力谋划能力的行动者,从而将她们排除在伦理图景之外。
然而,什么是作为伦理生活根基的“关怀”,伦理学家们并未达成一致。其中,美国学者Joan Tronto给关怀下的定义流传甚广:关怀是“一种活动,包括我们为维护、控制和修复我们的‘世界’所做的一切,以便我们能够尽可能幸福地生活于其中。这个世界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环境。”[3]
但是,Tronto的定义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它过于宽泛,以致于几乎可以将人们的一切与他人相关的道德实践容纳在内,反而部分地掩盖了关怀本身的道德价值。将关怀伦理学引入有关护理机器人的伦理反思,我们需要补充关怀活动的两个额外特征。首先是它的具身性特征:和抽象的道德态度、道德动机或道德理由不同,关怀总是通过特定的外在活动和劳作来实现,它是一种包含着内在价值的实践;其次需要强调的,是关怀的向他性或者非自反性:关怀实践总是指向他者,在严格意义上,我们并不能关怀自己,并不能向自己提供所需的照顾。因为,即使我们可以说你要关心自己,你要照顾好自己,我们也不会认为这种自我关怀本身具有内在的道德价值。
在我看来,正是上述两个特征使得机器人也可以成为关怀的提供者,而且护理机器人或者说关怀机器人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不同寻常的伦理内涵。因为它所介入的乃是我们伦理生活的根基,是原来属于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关系。
护理机器人伦理反思的理论框架
在关怀伦理学视野的引导下,我们还有必要从不同视角来审视护理机器人存在和发生作用的不同方式。它可以帮助我们更系统地展示护理机器人在人类医疗卫生实践的不同层面上产生的伦理影响,从而为未来的伦理反思奠定更加坚实可靠的理论框架。
首先,护理机器人是物理存在。这个层面的伦理问题主要涉及操作安全性和环境友好性。这些问题大多可以纳入传统的机器伦理,通过引入或建立相关行业设计和生产标准、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来予以解决,保障护理机器人使用者的人身安全和维护环境可持续性发展原则。
其次,护理机器人对于保障病患和残障人士的健康需求和基本生活质量意义重大,它们并不单纯是卫生保健消费品,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开始成为公共医疗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它们往往造价昂贵,需要不断更新换代,同时又是决策者应该考虑公共资源分配、费用承担的问题;护理机器人还可能给就业造成冲击,不过,它们的应用同样有机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如机器人的监控者。
第三种看待护理机器人的方式是将它们看作数据载体,护理机器人直接接触与个人身体、心理、社交等相关的数据,而且可以出现在家庭这样的私人场所,它会接触和搜集大量的个人身份敏感信息,由此产生的信息安全和隐私问题尤为严峻。机密性、隐私权和知情同意权是这个层面首先需要捍卫的基本原则,而这些基本权利也是人的自主权和人格尊严得以捍卫的重要保障。
最后,护理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体,还具有一定自主性。虽然它们并非独立的道德主体(moral agent),但也应该被看作独立的道德要素。护理机器人进入我们的私人空间和日常生活,会给我们带来更加严峻的伦理挑战。尤其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关怀关系的构成要素,机器人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于情感和相互依赖关系的根本认识,如何面对这些关怀关系的全新参与者,如何将它们嵌入我们与他人、与世界的交互网络之中,是我们必须通过充分的理论构想来回答的首要问题。
[1] A. Van Wynsberghe, Healthcare Robots: Ethics,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Farnham: Ashgate, 2015, p.62.
[2] J. Tronto, “Creating Caring Institutions: Politics, Plurality, and Purpose”, in Ethics and Social Welfare, 4(2), 2010, 158-171.
[3] J. Tronto, Moral Boundaries: A Political Argument for an Ethic of Care. New York, NY: Routledge, 1993, 103.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