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几篇《白话》专栏文章[1]中,我们提出一种假设,即人类新基因的出现引发语言能力,语言能力使得个体对周边实体辨识和对实体之间关系想像符号化,并外化成为居群共享的信息资源。这种外化的“符号化”能力加上人类创制工具的能力,形成了具有正反馈特征的、人类特有的“认知能力”。这种能力不仅表现为“器物工具”作为实体的媒介,提高了人类生存的核心即“三个特殊”运行中“相关要素”整合的效率,增强了运行的稳健性,还表现为“观念工具”作为虚拟的媒介,使居群成员之间得以交流各自在行为方式上的选择(所形成的共识最终表现为“文化”,即习俗、观念、制度),从而为人类在与生俱来的两个主体,即行为主体和生存主体之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关联纽带。
在实体和虚拟两种工具的互作下,人类认知能力在捕猎过程中初试锋芒,就引发了捕猎模式的改变。不仅在人类所到之处带来了各种大型动物灭绝,而且也将人类自身逼入了只有“吃草”,即依靠周边植物种子落粒性基因发生的变异,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侍弄植物(农耕),才得以苟活的境地。
01
农耕是人类演化之路的意外之喜?
其实,大家没有必要为我们祖先的困境担忧。人类能够在地球上存活至今,并成为地球生物圈中的一个主导物种,说明我们的祖先最终在他们的祖先因认知能力所造成的困境中走了出来。如果将工业文明出现之前地球上生活在农耕社会和生活在采猎社会人类的生存状态做比较,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前者占据绝对优势。如果说进入农耕是人类认知能力运用于捕猎过程而引发的捕猎模式从“弱肉强食”改变为“擒贼擒王”、造成猎物灭绝而不得不面对的结果,为什么人类反而因祸得福,获得了一种更有利的生存方式呢?
有关农耕和采猎孰优孰劣的问题,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有大量的研究。我作为植物研究者,没有资格置喙这类问题。但我在本专栏之前一篇文章中[2]提到的一个困惑,好像与这个问题有一点关系。在读本科时,我曾为育种家千辛万苦选育出来的品种为什么会在使用过程中“退化”而感到困惑。后来我意识到,育种家所选育的“性状”(如高产优质)是以人的需求为对象的。可是,植物生长过程中各个部分比例关系是在与其周边“相关要素”的整合过程中,在对自身而言“适度”的原则下迭代的结果。
我记得当时上作物栽培课时,老师一直强调“良种”要有“良法”。“良种”是育种家关心的事情,而“良法”则是栽培家关心的事情。我当年“弃农转理”是因为感觉农学更多的是关注结果,而我自己更感兴趣机制。但几十年之后我发现,从“整合子生命观”的视角再看当年老师所说的“良法”,不就是通过人为干预,为植物生长提供其在野生状态下不具备的“相关要素”,从而迫使植物突破在其自身演化过程中形成的“适度”范围,形成人类所需要的“性状”吗?
如果我对“良法”的解读是成立的,那么或许农耕最终优于采猎这个结果背后,蕴含有不同于传统解读的更加深层次的道理。
02
一籽落地,万粒归仓:
人类生存资源获取模式的转型
我们前面提到,“认知能力”的出现驱动人类在捕猎模式上,出现了从其他动物的“弱肉强食”转变成为“擒贼擒王”。“擒贼擒王”的捕猎模式虽然高效,但本质上仍然与其他动物一样,依赖于猎物或者取食对象的自我更新能力而获取生存资源(“三个特殊”运行所需的“相关要素”),或者说人类仍然作为食物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受到网络周边其他节点消长的制约。这就是为什么“擒贼擒王”造成猎物种群崩溃之后,人类不得不从“吃肉”改为“吃草”。
转入农耕之后,情况在不知不觉中出现了变化:最初,人们只是因为植物落粒性基因突变而得以集中采收植物种子作为食物[3]。可是,当人们发现原本采集来作为食物的种子,居然还可以发芽而形成新的植株并成为采集对象之后,种子的属性在原本只是作为“食物”之外,被人类赋予了作为产生更多种子源头的内涵。《说文解字》中“种”字的解释是“先穜後孰也。从禾重聲”。英文中seed的词源与sow,即“播种”同源。在两种语言中,“种子”这个“符号”都被赋予了双重含义。
我在小时候就知道“一籽落地,万粒归仓”。后来我的好朋友张大明告诉我,此话衍生自唐朝李绅的《悯农》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种子从被采集的“食物”,变成产生食物的源头。而这恰恰意味着,人类获取生存资源的方式出现了根本的转变——从原来和其他动物一样,依赖于猎物和其他取食对象(如猴子吃的香蕉、黑猩猩吃的无花果[4]和钓的蚂蚁)的自我更新,转而依赖于对从“一籽落地”到 “万粒归仓”(注意,这里不是全部的种子)的植物更新过程的干预(同理适用于其他驯化动植物)。采集野生植物的种子作为食物的获取生存资源的方式本质上只是和其他动物一样的“取食”,而通过播种(sow),从人工培育植物(类似过程也适用于驯化动物)生长过程中的“增殖”部分而获取生存资源的方式,我将其称之为“增值”。
03
突破“食物网络制约”:
在生存模式上与其他动物分道扬镳
对于“取食”这种获取生存资源的方式而言,“食”的量取决于捕猎采集对象的自我更新状态。而对于“增值”这种获取生存资源的方式而言,“食”的量除了取决于培育对象自身的更新能力之外,还取决于培育者对培育对象更新能力的观察和理解,以及对更新过程的干预。
在这个过程中,培育者和培养对象之间整合成了一个全新的、具有自我迭代特点的整合子——培育者从对培育对象生长过程的干预中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而培育对象也把培育者的干预(或者侍弄)作为不同于其野生近亲的“相关要素”,从而成为新的动植物类型。
如果将上述“增值”过程的构成要素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增值”至少包含三个要素:增值的对象、增值的方式、增值的过程。显然,这三个要素都依赖于人的认知。从人类农耕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整个农耕历史就是上述三个要素之间在“认知能力”的参与下,具有正反馈互作属性的迭代过程。
在上述过程中,“外化”的“认知能力”辨识与想像的对象显然超越了器物工具的层面,进一步把器物工具的作用对象,即培育对象也整合到了整合子的运行过程中,成为“相关要素”的全新类型。全新“相关要素”类型的加入,不仅拓展了人类自身“三个特殊”运行的时空尺度,还进一步提升了 “三个特殊”运行的效率和稳健性。其结果类似于形成了一个更大的“居维叶漩涡”(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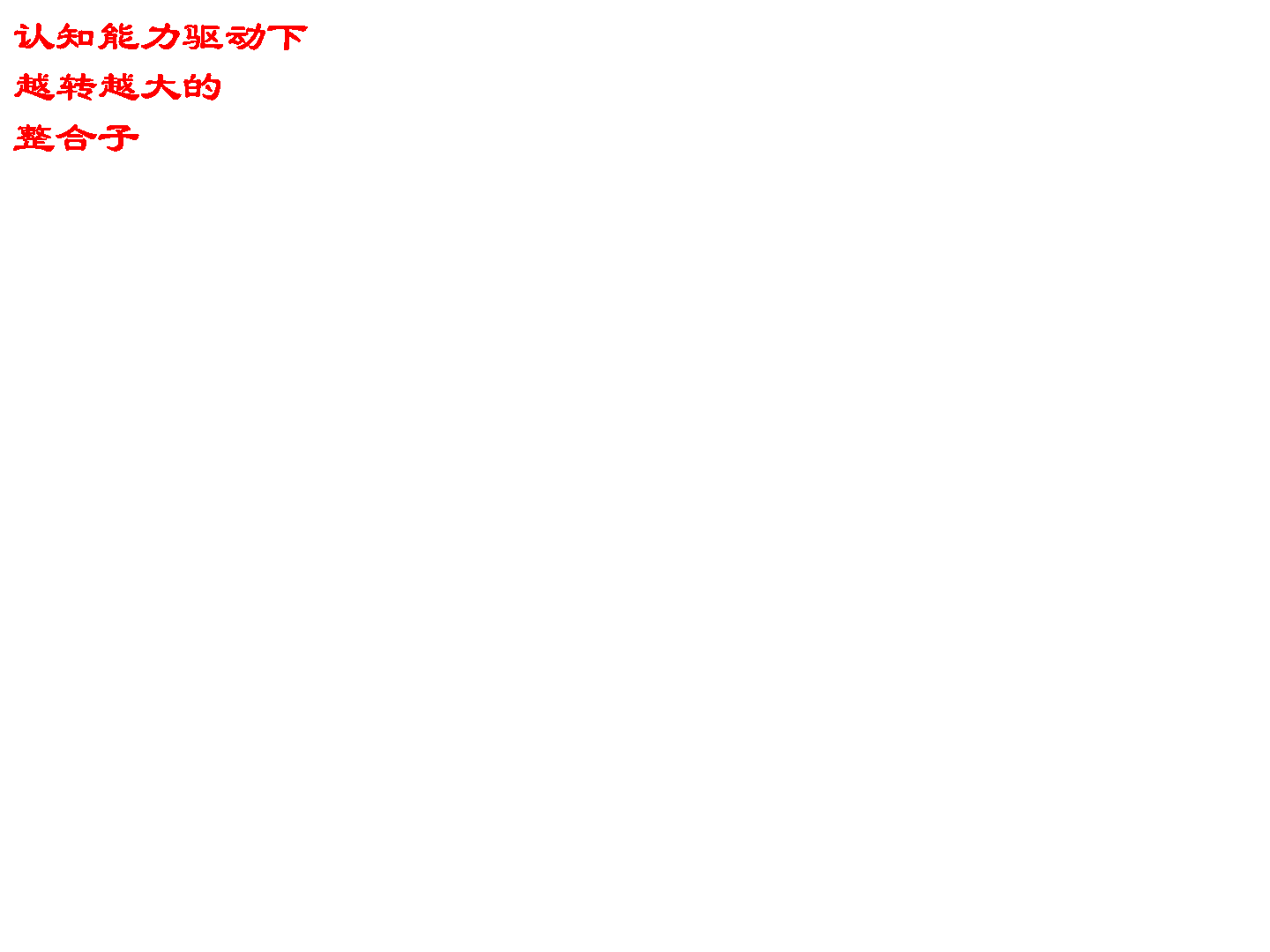
图1
从“人”作为一个生命系统的视角来看,原来因不得不“吃草”而衍生出来的生存资源获取方式上从“取食”到“增值”的转型,居然为人类的“认知能力”提供了一片全新的用武之地。这不仅让人类因祸得福地发展出了一种全新的生存资源获取模式来维持自身的生存,还因为这种生存模式在认知能力驱动下的正反馈属性,使得人类能够借助干预而逐步掌控生存资源的生产,并因此而开始减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原本“取食”对象自我更新能力的依赖。摆脱对“取食对象”原有自我更新能力的依赖,意味着人类开始有机会突破地球生物圈所有其他动物种群发展,不得不服从的“三组分系统”中“食物网络制约”。这种突破对于人类而言,是走出动物世界,在生存模式上与其他动物分道扬镳的演化道路上迈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大步。
我之前在栏目“n问•白书农4”[5]和文章《疫情之后,人类社会向哪里去》[6]中提到,动物居群,即生存主体得以维持的机制是“三组分系统”,即“秩序(个体行为模式/规范)”、“权力(维持秩序的力量)”和“食物网络制约(界定秩序和制约权力的要素)”三个组分之间形成的具有正反馈属性的相互制约。
我们已经在上篇文章《酋长的标志》中看到,人类认知能力应用于捕猎过程的“初试锋芒”就改变了动物世界演化千百万年所形成的“弱肉强食”的捕猎模式,不仅在人类所到之处无不带来大型动物的灭绝,而且也让人类自身陷入“吃草”的困境。那么,因农耕而出现的“增值”的生存资源获取模式打破“食物网络制约”,在生存模式上与其他动物分道扬镳,除了帮助人类化解捕猎模式转型所带来的困境这种“正效应”之外,会不会产生什么始料不及的副作用?我们在下一篇文章中讨论。
艺萌「睿ⁿ」 | 编
注释
[1] 参见《白话》专栏文章《脱实向虚与人之为人I》、《脱实向虚与人之为人II》、《酋长的标志》。
[2] 参见《白话》专栏文章《传什么“宗”,接什么“代”——什么叫一个“物种”?》
[3] 植物在野生状态下种子的成熟是不同步的。这是植物在与不可预测的环境因子变化互动过程中演化出来的一种特点。但这种特点使得采集者很难一次收获大量的种子。
[4] 央视译自BBC的纪录片《黑猩猩》[黑猩猩]丛林中的黑猩猩家族 (cctv.com)
[5] 参见“n问•白书农4”《动物世界千姿百态的生命活动有共同规律可循吗?》
[6] 白书农:《疫情之后,人类社会向哪里去》,宋冰主编,《走出人类世》,中信出版社,2021年。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