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期文章中我们提出对“三个特殊”相关要素整合媒介的“符号化”,不仅可以让不同个体在代表“相关要素”特征的物理化学信号可接收范围之外,了解周边实体迭代存在,由此拓展的“三个特殊”相关要素整合的空间尺度,还可以借助符号而实现生活经验的代际传递,从而拓展“三个特殊”相关要素整合的时间尺度。以此提出,语言表达能力为人类生存带来了全新的生存优势。但是,这个判断面临一个挑战,即鸟语算不算“符号化”。
Jared Diamond曾经在他有关语言起源的研究[1]中提到过采猎部落语言相对简单的现象。为什么停留在采猎阶段的人类相比于进入农耕阶段的人类,在语言形式和内容上都会相对简单呢?是因为基因或者因为基因所决定的人体结构吗?我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研究证据。但有一个现象却可以对基因决定论提出质疑,即很多出生在封闭落后地区的人进入发达城市之后,可以很快地掌握在其出生地的人们从来不会使用的语言(比如学外语)。如果采猎部落语言相对简单的现象不是基因或者人体结构造成的,那么还有什么可能呢?
01
“认知能力”大概是人之为人的奥秘
其实,如果仔细分析人类语言的构成和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在发声和加载信息两个要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但在有文字记录之前很难保留下来作为今天研究对象的要素,即被“符号化”的信息内容的迭代!我们无法知道鸟类或海豚借声音而传播的信息中,究竟有多少代表周边实体的符号;但我们可以知道,相比于采猎部落的语言,有文字记录社会的符号要复杂得多。如果这个判断是成立的,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两个非常有意思的比较:
一个比较是,虽然鸟类或海豚都可以如人类那样借助声音来交流对周边实体的感知,它们的语言当然也属于“符号化”,但它们的身体结构决定了它们难以改变周边实体的存在形式,因此需要被交流的信息也只能限于既存的周边实体的相关信息。而人类却因为能够利用工具改变周边实体的存在,使得可供交流的信息或者符号随工具的改进和对周边实体的改变而不断增加,从而最终在可利用符号的种类和数量上与鸟类和海豚等动物产生实质性的差别。
另一个比较是,虽然黑猩猩、僧帽猴等灵长类动物也能借助工具改变周边实体的存在,可是就目前所知,它们很不幸地缺乏借助声音来交流声音信息的身体结构。因此,尽管从Eve Spoke报道黑猩猩可以学会人类手语开始,不断有研究认为黑猩猩、倭黑猩猩甚至大猩猩可以学会人类使用的抽象符号(如手语和图解)[2],但这些人类近亲却无法自主形成类似人类的语言表达能力,并衍生出复杂的符号系统。
基于上面两个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以语言表达能力为特征的“符号化”并非人类特有,但在其他生物中,这种能力无法与基于其他身体结构为基础的利用工具改变周边实体的能力相结合,“符号化”所带来的生存优势难以自主迭代。只有“符号化”与人类利用和制造工具而改变周边实体存在形式的能力及其表达需求相结合、借助声音而传播的“信息”得以迭代之后,“符号化”所带来的“三个特殊”相关要素整合的时空尺度的拓展,才能形成一个正反馈系统:不仅更高效地利用既存的“相关要素”,还可以借助改变周边实体的存在形式而不断创造新的“相关要素”。
考虑到“符号”和符号的处理都属于信息处理功能,我们将因工具创制而衍生出的、具有自驱动迭代特征的“符号化”能力称为“认知能力”。或者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表示:认知能力=形成符号的抽象能力+传播符号的语言能力+衍生新符号的工具创制能力。从这个角度看,如此定义的虚实结合的“认知能力”大概是人之为人的奥秘?
02
人类的“好奇心”是打破脑平衡的后果
其实,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相信很多读者从类似《动物世界》的纪录片中可以看到,在野生动物的居群中,只有幼小阶段的动物不停地上蹿下跳,而成年动物吃饱后基本上就在闭目养神。这其实反映了成年动物的行为驱动力无非是取食、避死和求偶。从整合子运行[3]的角度讲,动物最核心的行为驱动力就是“取食”。而驱动“取食”的动力当然就是“脏腑饥饿”。
人首先是一种动物。所谓“民以食为天”,讲的其实就是“脏腑饥饿”。但人类为什么吃饱了还要忙乎呢?有人说是防患于未然,有人说是贪婪。其实,从上述基于语言能力的“符号化”与“工具创制”之间形成的正反馈关系我们可以发现,人类所出现的不同于其他动物的行为模式背后,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提到,有“脑”的动物对于周边“相关要素”的整合过程,都需要对周边实体的辨识和理解。显然,作为神经中枢的大脑对相关信息的处理能力,应该与其生存所需处理的信息量相匹配。能力不足将无法生存,而能力过剩则是一种浪费。如果这个判断是成立的,那么我们可以将绝大多数动物吃饱了就闭目养神的现象,作为一种动物行为的默认状态。
以此为参照系,再看人类认知能力出现之后会发生什么:在工具的帮助下,人类“三个特殊”相关要素的整合,或者广义上的“取食”效率会得到提高(否则“工具”将失去其应有之义)。这种取食效率提高大概源自两种变化:第一,“符号化”提升了大脑对相关信息的处理能力;第二,取食效率提高意味着为满足生存所需处理的信息量可以降低。这一升一降会衍生出一个后果,即打破原本在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大脑信息处理能力与所需处理信息量之间的平衡。打破这种平衡又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对于受过基础教育、尤其是关注过科学发现的人来说,“好奇心”是一个不会陌生的概念。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人们对“好奇心”的生物学基础做过分析。我在“好奇心”的驱动下,曾经去查过英文curiosity(好奇心)一词的词源。检索的结果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惊喜:在dictionary.com网络词典中,一个老版本的词源注释是这样的:from Latin cūriōsus taking pains over something, from cūra care。“Taking pains over something(因某事而痛苦)”,即某种身体上的不适,是不是打破脑体平衡所带来的后果呢?如果是,可不可以认为人类“好奇心”的生物学本质,就是因为认知能力发展而衍生出的信息处理能力和所需处理信息量之间平衡破缺的表现形式之一呢?
03
认知能力的衍生物——“感官饥饿”
在我的知识范围内,没有见到过这方面的研究。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要化解因脑体平衡被打破所带来的身体不适,大概只有两种办法:或者是降低大脑对信息的处理能力,或者是寻找或者创造新信息供给大脑来重建脑体平衡。由于大脑对信息处理能力的提升是一系列演化事件正反馈迭代的结果,估计要降低大脑对信息的处理能力并不容易。于是只有后一种方法来重建脑体平衡。如果我们把驱动取食的动力称为“脏腑饥饿”,那么驱动寻找或者创造新信息来重建“脑体平衡”的行为,其动力不是可以被称为“感官饥饿”吗?
目前,“感官饥饿”只是我从不同的观察和推理中提出的一个概念。至少我没有从别处看到类似的说法,自然也没有看到支持或者反对这个概念的实验证据。但“好奇心”驱动人们探索未知,却是一个被大家广为接受的说法。如果接受“好奇心”是人类行为驱动力的说法,而且把“好奇心”看作“感官饥饿”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感官饥饿”显然应该被视为一种人类特有的行为驱动力。正是在“感官饥饿”的驱动下,人类不得不去尝试各种看似“无用”的行为。在行为开始之前,其实没有人知道这些行为会产生什么后果,更谈不上行为是“有用”还是“无用”。但在行为出现之后人们可以发现,这些行为中有些为人们带来了全新的生存空间,因此被后人作为“生活经验”而流传;有些不过是消磨时光,但其中一些变成了后人眼中的“艺术”;有些则对人类生存带来了危害,于是成为后人口中的“禁忌”。
无论“感官饥饿”驱动的行为本身具有多大的不确定性,作为“认知能力”衍生物的“感官饥饿”为人类行为引入了其他动物所没有的驱动力。“认知能力”借助语言把个体生存经验外化,成为居群成员共享的生存经验,而“感官饥饿”的出现又使得“认知能力”发展所带来的生存效率提升被“内化”,成为新的行为驱动力。两种机制互动,迭代出一个更高层级上的正反馈机制。这种全新的正反馈机制再和“脏腑饥饿”虚实结合(图1),如同启动了一台可以自制燃料的发动机——在它的轰鸣声中,人类被推上了一条充满不确定性的“认知决定生存”的演化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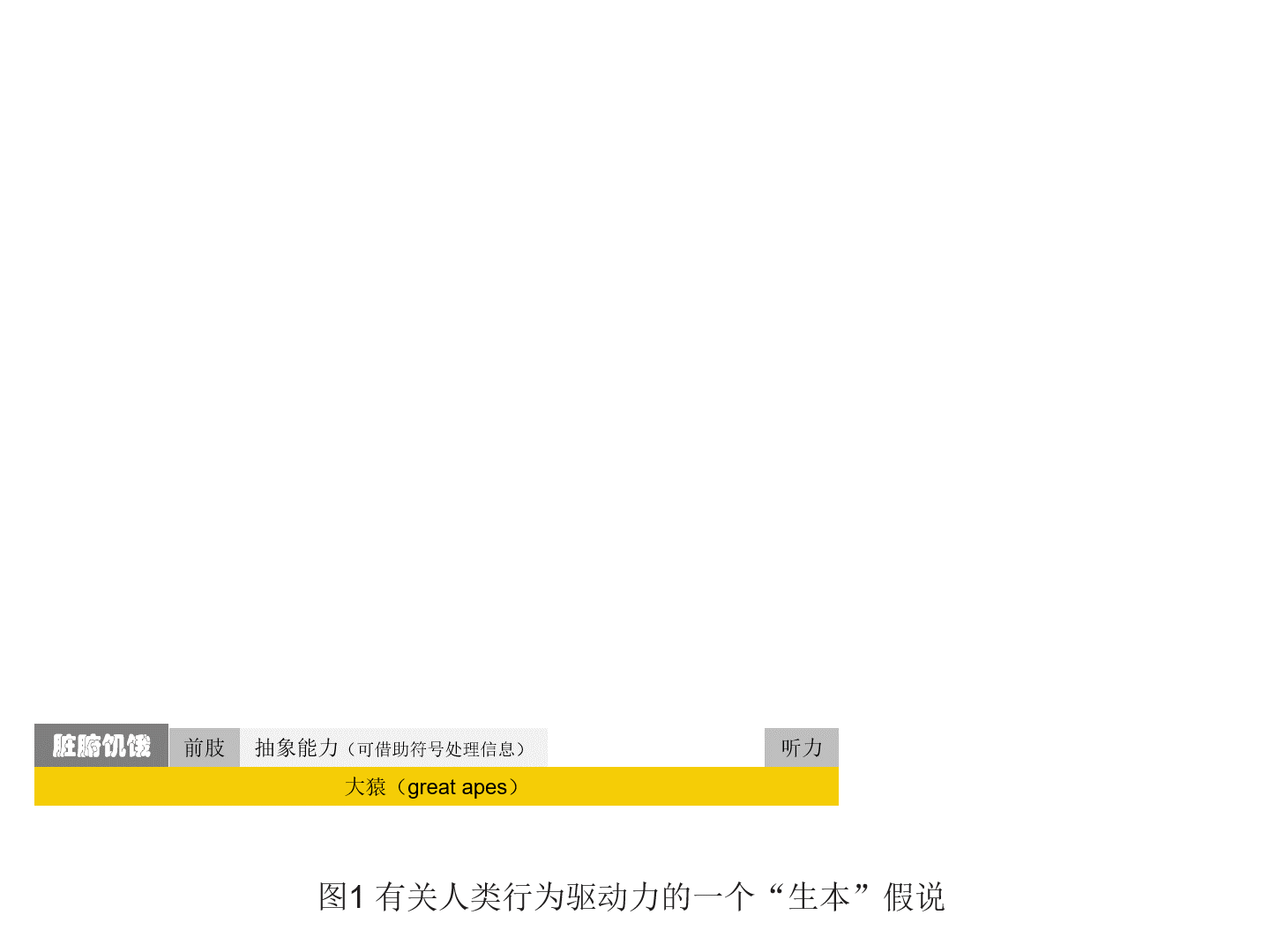
艺萌「睿ⁿ」 | 编
注释
[1] Diamond (1995) The evolution of human inventiveness. In What is Life? The Next Fifty Years. Speculations on the future of biology. Ed. Murphy MP and O’Neill L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视频,科科:与人类交谈的大猩猩
[3] 在白话专栏的前期文章中,我们提出生命系统的起点是“特殊组分(碳骨架组分)”在“特殊环境因子(如水、O2、CO2、温度等)”参与下的“特殊相互作用(以分子间力为纽带)”(即“三个特殊“)。这是一个以特殊组分互作所形成的复合体为纽带而自发形成的、作为热力学第二定律特例的非可逆循环。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论证了,整个生命系统,本质上就是以”三个特殊“为纽带而衍生出来的可迭代的生命大分子网络。因此,我们将生命系统不同层级的迭代状态给一个共同的名字,叫”整合子“,生命系统的运行,也因此而可以称之为”整合子运行“。更进一步的解释,可以参见本专栏的前期文章。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