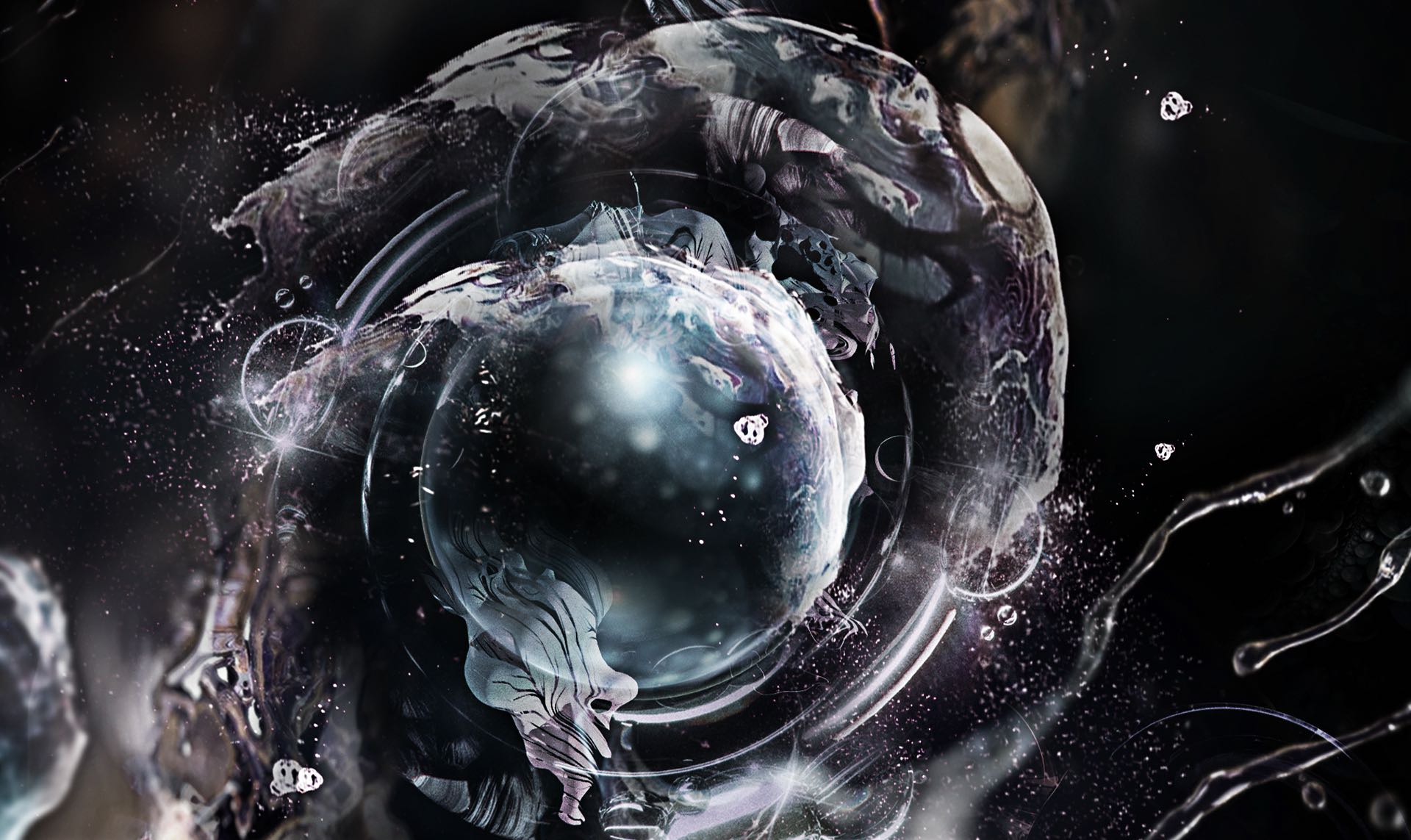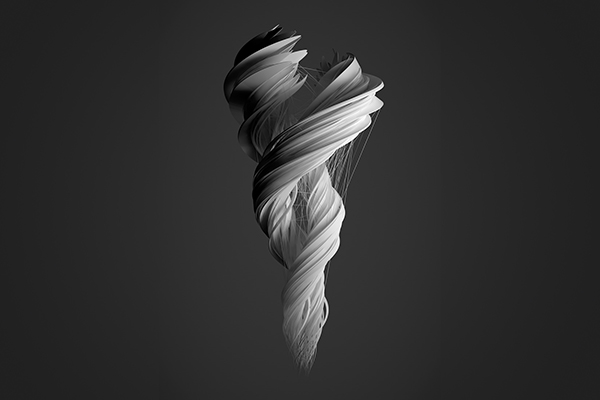当从哲学对概念思辨的角度和科学对实体描述的角度同时指向同样的生命现象时,会擦出怎样的奇妙火花?
01
真核细胞一定要以居群为生存主体吗?
这一组文章出来之后,大家好像对解释“真核细胞”是如何出现的“富余生命大分子自组织”假说没有太大的疑问,可能是因为这个假说对非生物学专业的读者而言太“生物学”,不宜置评,对生物学专业的读者而言太多的假设,无需(或不屑)置评。但不同的读者有一个共性的问题,即真核细胞为什么会出现两个主体性,即“行为主体是个体(单个细胞或者单个动物)”,“生存主体是居群”。与此有关出现了一个困扰,即既然真核细胞相对于原核细胞出现了结构的集约化和调控的优化,增强了细胞存在的稳健性,那不应该比原核细胞有更强的调控能力吗?怎么会出现了灵活性降低的副作用,以至于不得不依赖于细胞集合作为整体来应对“三个特殊”相关要素不可预测的变化呢?
有关“两个主体性”的问题,最简单的基于感官经验的回应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吃喝拉撒睡都得自己“亲自”来做,别人无法替代。但如果没有其他人的存在,比如父母,任何一个“个人”都根本不可能来到这个世界上。个体与居群在物种维持过程中发挥着彼此无法替代的不同作用。当然,这种解释在逻辑上是无效的。因为人类是多细胞真核生物,即真核生物中的一种。这种感官经验不过是关于“两个主体性”的举例,而不是对原因的解释。要深入地了解真核生物两个主体性的来源,还得多了解一点生物,或者有耐心等我的《生命的逻辑》写完出版。如果真正理解了“两个主体性”,那么真核生物需要以细胞集合(即共享DNA序列多样性的居群)来应对“相关要素”不可预测的变化,就是“两个主体性”的结果,无需多加解释了。
02
“无形”和“无”是不是一回事?
在《无形-有形-无形-……》一文发布后,有朋友在我的朋友圈中点评说:“应该是有,无,无也是一种存在”。写这个评语的是一位老朋友。他常常说我比较“哲学”。没有想到,他的评语却非常地“哲学”——关于对“存在”的本质问题的探讨。其实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讨论的只是实体的存在(此时没有“哲学”的意味,只是指可供检测的分子/原子基础的物质存在)可以有“无形”或者“有形”两种形式。而这两种形式的区分,首先是以人类的感官分辨力为参照点的。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组文章的第一篇加以讨论。
在《无形-有形-无形-……》这篇文章中,主要希望传递一个信息,即超越我们人类感官分辨力范围的实体存在,无论是微观的分子原子,还是宏观的群体——无论是无数水分子构成的汽团甚至台风,还是数不清的蚂蚁构成的蚁群(其实也包括天上的鸟群、非洲草原上的角马群、我们身边的人群),虽然身为人类的我们无法基于感官分辨力而了解其“形”,但它们却是对我们理解生命所不可或缺的存在。在我的观察中,这类存在常常被研究者下意识地忽略,从而衍生出很多难以解释的困境。一旦大家对这种“看”似“无形”的存在予以应有的关注,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03
“身在此山”的“山”有多大?
有性生殖周期(SRC)这个概念我是在2011年形成,在2013年借一篇约稿综述发表的(如果要说投稿,肯定没有杂志会接受发表。就算是夹带到约稿的综述中,约稿人还曾委婉地表示是不是可以不放进去)。在这个概念形成之初,我自己对这个概念意义的理解还没有到现在的程度。在表述上后来也做过两三次修正。但“有性生殖周期是一个被修饰的细胞周期”这一点,我却是在一开始就意识到了的。
在《两个主体与一个纽带——有性生殖周期》这篇文章发布后,有朋友在朋友圈中点评说,“这个细胞周期太长了”。我认为这个点评特别好。我对他的点评回应道:“正因为如此,才这么久没有被人类发现”。的确,这个概念本身一点都不复杂。只是大家对生活周期这个“过程”的观察过于拘泥于其“有形”的部分,而忽略了其“无形”、但可能更本质的部分,从而让我捡了这个“漏”。
还是回到人类认知对感官经验的依赖上。苏东坡曾有名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回到我们日常生活,尤其是研究工作中,我们希望了解的常常是超越我们维持生存所需的感官经验之外的事物(或实体存在的规律)。那么,这些“事物/规律”在多大程度/范围上超越了人类的感官经验?到什么程度/范围,我们可以判断其他事物与我们关注的对象已经没有关系了?怎么或根据什么来把握这个度?或者用小标题的话,我们“身在”的“山”究竟有多大?这其实是每个人思考过程中都无法回避的挑战。
04
求偶是为了传宗接代吗?
有一天在电梯里遇到邻居,他们正在议论另外的邻居家的孩子结婚生子的事情。其中的男士认为不结婚生子就没有完成人生的责任,因为没有把基因传下去。听到他们的议论,我深感传宗接代的传统思想遇到“自私的基因”,马上就可以换上“科学”的马甲。这个话题在外地来北大定量生物学中心参加暑假学校的本科生给的反馈中,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们关心的是不以结婚生子为目的的情感,有没有什么生物学上合理的解释。
对于求偶和传宗接代的问题,上面两种不同的反馈非常有代表性。前者的问题在于大家对一些近年生物学研究中的新发现缺乏了解,比如“生存主体”是居群、DNA序列多样性对真核生物的生存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而DNA序列多样性的重要来源,正是居群中作为DNA序列多样性载体的个体,它们是通过有性生殖周期这个纽带而分享各自的DNA序列来维持DNA序列多样性。正是因为求偶是为“居群”做贡献的“苦差事”,所以在动物才需要借助激素和神经系统的奖赏回路去予以刺激和鼓励、到人类则除此之外还要加上各种观念、习俗去予以要求甚至约束。
后者的问题在于年轻人没有意识到,人类的确是一种多细胞真核生物,的确服从多细胞真核生物的一些共同的规律。但人类又有其独特性,即我们将在第五组文章中讨论的“认知决定生存”的属性。这个属性决定了人类可以通过改变很多周边事物来维持自身的存在。这些“改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对“事物”的认知和理解程度。比如人类发明了避孕方法,从而使得求偶与生殖解偶联。但却并没有意愿去干预求偶行为本身,反而将求偶——在人类语言中加上很多人类社会演绎出来的文化要素后以“爱情”的形式的呈现,作为文学主题而津津乐道。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就不是其他生物共有的生物学问题,而是人类特有的社会学问题。不能简单地“还原”到生物学层面上去寻求解释。有关人类的独特性,我们将在第五组文章中专门讨论。
05
“类”以什么为标准来“聚”?
在《传什么“宗”,接什么“代”——什么叫一个“物种”》一文中,我们讨论了“物种”的概念。从生物学历史到人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分门别类不仅是生物学的首要问题,而且是人类生存的首要问题。分门别类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我们将在下一组文章中详细讨论。在生物学范畴中,“物种”作为一个节点概念大家一般不大会有争议。但有趣的是,什么是“物种”的标准,从我读书开始,就知道一直众说纷纭。
我到北大工作后,曾经在一门短命的课程上邀请到我的一位老师辈的大专家来给选课的同学讲什么叫“物种”。即便如此,我还是很久没搞明白在“物种”标准问题上人们争论在点究竟是什么。直到我自己动手写《生命的逻辑》时,去查了“物种”的英文species这个词的词源,方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词的词源是外观,appearance。这一下,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大家在这个问题上会出现那么多的纠结。
专业上的问题就不在这里多讨论了。只讲一点,即我在文章中提到,现代生物学语境下讨论“物种”这个概念,或者讨论“分门别类”这个过程时,“有性生殖”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关键节点——它不仅可以因个体间完成有性生殖而把同一居群中的成员关联起来,共享DNA序列多样性而成为同一个“物种”;而且还可以因个体间无法完成有性生殖而把不同居群的成员隔离开来(生殖隔离),成为不同的“物种”。
有人提出,因为没有有性生殖而把原核生物排除在达尔文演化理论中是不合适的。这个问题有点儿专业。很难用简单的话讲清楚。毕竟“物种”的英文在词源上就是外观,人们最初使用这个概念进行分门别类时,并没有考虑与有性生殖的关系。但后来知道,凡是涉及孟德尔遗传定律的地方,就无法绕开有性生殖。至于原核细胞和真核细胞的体细胞中起始细胞和产物细胞的关系,我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时的师姐发到我朋友圈上的一句评论非常精到:原有的(起始)细胞是两个(产物)细胞的来源,但不是这两个新细胞的父亲。
在生物学研究领域,人们常常喜欢说“凡事都有例外”。其实,很多时候,“例外”不过是因为人们对所谈论的事物或者被解释的过程了解不够的托词。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周洛华在他的《市场本质》一书中所说的那句话(尽管我并不认为他在书中为论证他的观点所引用的生物学例子是合适的):“得到广泛使用并不意味着这个词汇在使用中形成明确的约定俗成而不再模糊了,更可能的情况是越来越多的人在模糊地使用这个词,而没有感到丝毫不安”。
艺萌「睿ⁿ」 | 编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