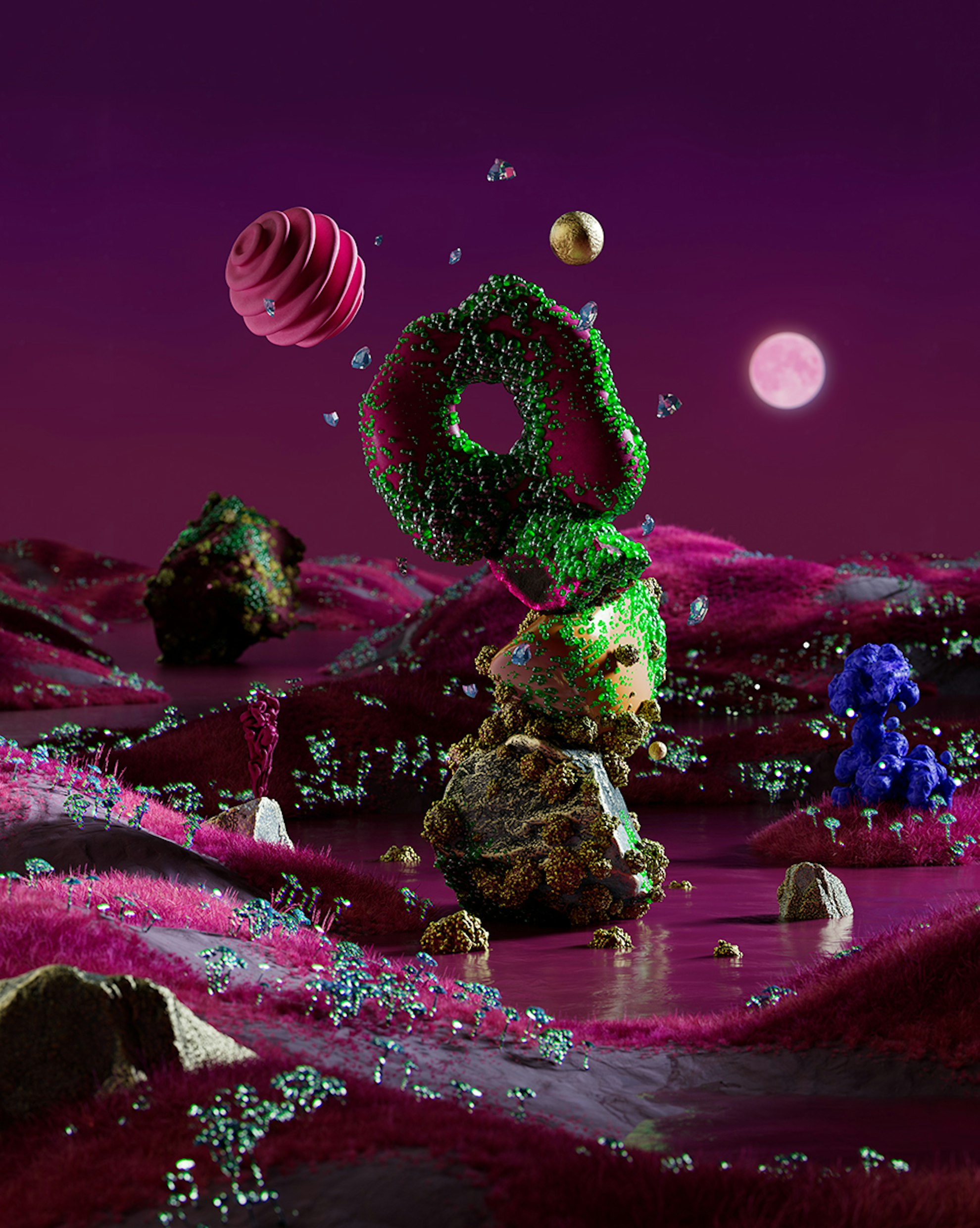元来到个处。不是今日新有底。
——宏智正觉(1091—1157)
在一万五千代人类的历史里,我们仰望守护星辰,感受无数存在性问题的重压:整个宇宙中只有我们吗?是否有其他行星环绕遥远的恒星?如果有,这些另外的世界是否也孕育了生命,抑或我们地球上上演的,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偶然?其他智慧和文明是否存在?是否也通过在制造工具和创造世界上的成功,将自己带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些问题的首次回答已初具雏形。就像五个世纪前哥白尼重新构想了太阳系的架构,我们再次身处一场以行星为中心的革命。一门名为天体生物学的新科学,已然改变了夜空。
它向我们表明,银河系中几乎每颗恒星都拥有一个由多个世界组成的家族。通过运用强大的新仪器和理论方法,我们也在学习如何在这些遥远的世界中寻找外星生物圈。未来几十年,我们或许最终找到这个古老问题的答案:在生命、行星和宇宙中,我们到底处于什么位置?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间尺度,对回答另一组关于生命和我们行星地球的问题也至关重要。在仅仅作为地球上的过客生活了这么多个世代之后,如今的人类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及其运行方式。我们的文明计划把地球推入了“人类世”——一个人类主导、充满危险意外后果和巨大不平等的时代。随着地球演化轨迹发生变化,我们共同生活的集体计划也在变化。该计划的未来,则有待定夺。
然而,人类世和天体生物学同时崛起并非偶然。二者都表明,人类第一次与行星与生命之间的真实联系相遇了。人类世的紧迫性和天体生物学的许诺,揭示了行星与生命——地球及其生物圈——始终在共同演化。无论发生于何处,生命及其寄居的行星都必须被看作一个动态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从这个角度来看,某种全新的东西正在出现,为我们当前跌跌撞撞走向灾难的局面提供了一个替代选项。如今,一种不同类型的人类未来成为可能。这种由全新的自我认知和自组织驱动的人类未来,被称为“行星观”(the planetary)。
“行星观”是一种新的“宇宙观”——作为全球现代性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秩序的替代方案而出现。“行星观”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范式,根植于关于生物圈和其支持行星的革命性科学进展。它还能帮助我们洞察已经建成并正推动人类世发展的“技术圈”(technospheres)的命运。以此科学为框架,行星观为我们在气候变化世界中的未来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鉴于其潜力,行星观值得我们关注和理解,如此,我们亦可懂得怎样在漫长的进程中给予滋养,直至其开花结果。但该潜力之广泛,也要求我们跨越广阔旷野,领悟包括系外行星的发现、盖亚理论的认可,以及复杂性科学作为生命新理论的精妙之处。综合起来,我们才可以看到所有可能性中最重要的那种:一种革故鼎新的“行星智慧”,人类文化和生物圈在其中共同繁荣直至长远的未来。
行星观的观点令人振奋。人们一路走来不虚此行。更重要的是,它还提供了一种只有行星才能给予的东西:一个新的视界。行星观的视界有着广阔的机会空间,只要我们有勇气和远见去蹚,就能蹚出一条通往另一种未来的路。
“就像五个世纪前哥白尼重新想象我们太阳系的架构那样,我们再次身处一场以行星为中心的革命。一门名为天体生物学的科学已然改变了夜空。”
哥白尼革命中被颠覆的是什么
在公元1500年的时候,大多数识字的欧洲人(当时这样的人并不多)每天早上醒来,都认为太阳从地平线升起。这是因为人人皆知太阳绕着地球运转。我们的星球是宇宙的固定中心。
快进几个世纪,大多数识字的欧洲人每天早上醒来都知道不是太阳升起来了。相反,是地球的地平线下降了。如今人人皆知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地球只是受其引力影响的一个行星。
对大多数学者来言,哥白尼对太阳系的重新排序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科学革命的诞生。然而,我们后来所谓的“哥白尼转向”不只影响了科学。在所有席卷欧洲(以及最终席卷整个世界)的重大变革中——包括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经济的兴起,我们都能感受到这一转向的影响。
在《科学宇宙观和国际秩序》(Scientific Cosmology and International Orders)中,政治学家本特利·艾伦(Bentley Allan)探索了过去五个世纪的重大科学革命及其与文化的互动。艾伦也展示了这些革命是怎样在政治和经济的动态变化中得到表达的。科学在驱动物质变革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它得以重塑欧洲的文化想象。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学革命也改变了艾伦所说的“宇宙观”——既包含文化的背景认识论,也包括其本体论。
在总结艾伦的研究结果时,哲学家卢卡斯·利卡夫坎(Lukáš Likavčan)清晰表达了这些最大规模的科学与政治变革之间的关联。利卡夫坎在一篇即将发表的文章中写到,“新兴的科学宇宙观限制并决定了国际秩序的制度组织、地缘政治变革的动力机制和国际经济体系之性质的默认视角”。因此,宇宙观的转换超越了科学范式的狭义定义。正如艾伦所言,这些转换成了新的宇宙观假设“被引入政治话语”的时刻。科学最初的探索,最终发展为社会想象自己所处的文化、政治和权力宇宙。
科学与政治—文化耦合的第一个时代,始于哥白尼革命。它一开始只是一种纯粹天文学的、对行星架构的重新构想,后来却成长为某种更广泛的东西。在伽利略和后来的牛顿给哥白尼的新太阳系加上惯性与力的因果说明之后,一个新的宇宙观出现了。那是一个唯物主义、理性、数学上可表述为不变的物理学定律的宇宙。这种宇宙观,取代了延续已久的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和天主教神学的综合体系。
十六、十七世纪出现的这一新科学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行之有效。在被应用于航海导航和军事装备那样广泛领域的时候,它造就了非凡的财富和权力。鉴于其效力,科学的力量被有权有势的人利用也就不足为奇了。据估计,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会(现称皇家学会)的创始成员约三分之一是王室官员。例如,科学新方法的积极倡导者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同时也是大法官。
新兴科学机构和既有的政治机构之间,存在着精英的频繁流动。通过这些对话和交流,人们日益倾向于通过一个唯物主义的、机械论的视角来看待自然和人类世界。科学宇宙观就这样重塑了政治经济学的宇宙。
以神的旨意来统治自己及国家的君主时代在逐渐结束。正如艾伦写的,“在十七世纪,世袭国家目的的主导地位,让位于新兴的‘利益’”。这些“利益”可以被理性化和定量化,以表格的形式表达,而表格本身就代表了唯物主义和机械论对如何利用物质的理解。政治不再为延续王朝服务,而是一种平衡权力的定量计算。深具机械论色彩的形象,被明确规范为国家间关系的准则。
在上帝被逐渐淡化为一种自然神论(这种自然神论起到的唯一作用,是让机械定律运转起来)的同时,大臣和外交官们创建了一种新的机械社会秩序。因为哥白尼和牛顿把太阳系重新想象为钟表机构,所以,它之上和之下的一切也都变成了机器。这也包括直接从科学发展出来的新的、展现野蛮效率的工业经济。
一场天文学家之间关于天体运动的争论,竟然帮助重塑了整整一个大陆(以及随后世界大多数地区)的政治现实——这着实引人注目。不过,这就是行星在人类想象中的力量。哥白尼革命的历史影响既深刻又广泛。
这就是现在我们为何必须关注那场正在进行的、认识宇宙中生命的革命——我们将称之为“天体生物学转向”。这一世界观的转变,为正在展开的新行星宇宙观奠定了基础。
“随着地球演化轨迹的改变,我们在地球上共同生活的集体计划也在变化。我们这一计划的未来也悬而未决。”
地球成了系统,气候成了问题
1995年,第一颗围绕类太阳恒星运行的系外行星被发现。那是一个划时代的时刻。天文学家关于太阳系外是否还有“众多世界”的问题,已经争论了两千五百年。这颗离地球五十多光年的飞马座51(室宿增一)类木星行星的发现,彻底结束了这场争论。但1995年并非行星观及其新兴宇宙观的起点。事实上,早在几十年前,科学界就已开始从天文和行星学的视角重新审视地球上的生命。
二十世纪初,生命对地质学家的吸引力微乎其微。生命被认为是独属生物学家的领域,对地球历史的大多数物理和化学机制似乎没有产生重大影响。直到伟大的俄罗斯科学家弗拉基米尔·维尔纳茨基(Vladimir Vernadsky)提出,生命也是一种行星力量(planetary force)。地质学家出身的维尔纳茨基极具远见地第一次完整定义了生物圈这个概念。
他在1926年出版的著作《生物圈》中写道:“……生物圈的物质收集并重新分配太阳能,并最终将其转化为能在地球上做功的自由能……倾泻到地球上的辐射使生物圈获得了无生命行星表面无法具备的特性,从而改变了地球的面貌。”
维尔纳茨基将生物圈视为一个活跃的地球物理系统,打破了生命只是附着于冷漠行星表面的绿色薄膜这一观点。他的生物圈视角,也奠定了共同演化这一关键概念的基础。地球的生命是一个整体,既被行星非生命系统的变化所驱动,同时也驱动这些变化。
大约五十年后,差不多在太空时代到来之时,人们才对生物圈和共同演化的能力做出了进一步的阐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化学家兼博学者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受雇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为探索月球和火星的任务设计生命探测实验。在思索如何在与地球完全不同的星球上寻找像地球一样的生命这件事时,洛夫洛克突然意识到,行星的大气本身就能帮助探测生命。那时,他在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与年轻的卡尔·萨根(Carl Sagan)共用办公室。
在思索生物圈可以如何改变其所在行星的过程中,洛夫洛克意识到,生命会将行星大气推向在无生命行星上不可能出现的化学状态。在无生命行星上,像二氧化碳、甲烷那样的大气分子会与其他化合物反应,直至达到一种平静、死寂的均衡。而在有生物圈的行星上,生命会持续地向大气排放像氧气那样的新气体。因此,生物圈的持续“呼吸”是行星级新陈代谢的产物。它使大气保持在远离无生命世界化学平衡的状态。
凭这一灵光乍现,洛夫洛克看到了天体生物学的未来。通过寻找大气化学不均衡的迹象,天文学家或许能在遥远的世界中发现生命。不过,循着这个思路,他们发现的将不仅仅是单个外星物种的证据,而是生机勃勃的行星级生物圈。
理解到生命有改变整个行星大气层的力量,是洛夫洛克对天体生物科学做出的持久贡献。但洛夫洛克对生物圈力量的洞察不只是一种试验方法,也是他发明“盖亚理论”的基础。
盖亚理论起初被称作“地球自调节系统理论”,该理论认为,地球上的生命出于自身目的改造了这颗星球。具体而言,就像我们在这颗星球的历史中看到的那样,生物圈对这颗星球的无生命部分施加了强反馈。这些反馈把世界维持在一个宜居状态。无论外部条件如何,人体的平均温度都保持在98.6华氏度。洛夫洛克认为,有生物圈的行星也可以实现一种类似的内稳态(homeostasis):它们会自我调节。
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很快也加入进来,和洛夫洛克一起发展盖亚假说。她的主要贡献来自于对地球丰富的微生物生态系统的详细了解。正是马古利斯意识到微生物有能力驱动洛夫洛克提出的行星自我调节机制。
在当时,盖亚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宏大想法,它要求从根本上重估生命及其在行星尺度上的演化。不出所料,洛夫洛克和马古利斯遭遇了巨大阻力。不过,他们的努力很快就被置入另一个语境,这个语境改变了科学界对盖亚理论中关于生物圈力量的看法。
人类活动正在改变地球气候的可能性,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就被海洋学家罗杰·雷维尔(Roger Revelle)所指出。1965年,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甚至在国会演讲中提到了气候变化。到八十年代中期,人为化石燃料对气候的影响终于在测量数据上得到体现。众所周知,1988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午后,气候科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在国会面前作证,气候变化已经发生。
盖亚理论对研究和承认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不容低估。盖亚理论的一些方面依然存在争议,比如说,生命在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劫持一颗行星这件事情上可以做到多彻底。但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人们普遍认为,生物圈(及其人类子嗣)是驱动地球环境条件改变的重要力量。
从盖亚理论也衍生出一种谈论“耦合的地球系统”的新语言。最初,无生命系统构成了行星系统:空气(大气圈)、水(水圈)、冰(冰冻圈)和岩石的上层区域(岩石圈)。这些统称为“地圈”。它们彼此“耦合”并与构成生物圈的有生命物质耦合。科学家们所说的“耦合”,指的是一个系统的变化会引起另一个系统的变化。如果大气圈中的温室气体增加,那么冰川会融化,海平面会上升,海洋对陆地的侵蚀会加剧,生命也会改变其生活场所和方式。
随着气候科学家开始从这些耦合系统的角度来研究气候变化,盖亚理论也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即地球系统科学(Earth Systems Science, ESS)。正是通过ESS领域研究的推进,气候科学才有所进步。通过把生物圈和其他非生物地圈置于同等的地位,人们汇总出了关于人为气候变化的全面叙述。
地球系统科学是跨学科的新型科学,是理解行星观及其视角何以引起更广泛的文化宇宙观变化的关键。在ESS领域中,以往彼此孤立的学科之间的旧有界限开始相互渗透。要科学理解全球变暖,研究者需要建立新的认识论,把地球当作一个“复杂系统”来理解。而“复杂系统”这个术语本身,就是一个新出现的科学词汇。地球不再被视为一团死寂的岩石球体,而是由地质、生物、社会系统和技术交织而成的嵌套网络。这些网络共同在地球上传输巨大的能量、物质和信息。盖亚理论最早提出了这种惊人、宏大的行星与生命的视角,而地球系统科学则专注将这一视角具体化。
推动地球系统科学发展的国际压力,使得作为范式和宇宙观的行星观应运而生。这是一种新的世界系统,是基于对生命和作为复杂整体的行星的新科学认识。在关于全球政治秩序和政治经济的激烈争论中,人们迈出了通往一种新的行星观的第一步。到二十世纪最后十年,行星观的核心观念已经成为有关气候变化和人类未来的基础文化辩论的中心。行星观作为一种视角开始关注新类型的问题,同时,行星观作为一种宇宙观也逐渐成形。
“如今,一种不同类型的人类未来变得可能。这种由全新的自我认知和自组织驱动的人类未来被称为‘行星观’。”
我们将如何发现生命
行星观持续涌现的下一步,与1995年人类首次发现围绕类太阳恒星运动的系外行星密切相关。不过,到二十一世纪头十年末,发现此类行星的速度大幅加快,天文学家得以编制出一份后来得以验证的外星世界目录。现在,我们知道地球只是宇宙中多达一百亿兆个潜在宜居星球之一。随着每天新的系外行星被发现,我们正迈向下一阶段,即在地球之外寻找生命。
在物质层面,这一探寻将依赖新一代高精度望远镜来进行,这些望远镜能够捕获来自遥远系外行星的光谱,并对其进行详细分析。尽管这种技术上的突破令人惊叹,但并非什么新鲜事。整个现代历史都伴随着技术进步的书写,包括推动人类世巨大加速的那些技术进步及其引发的人为气候变暖。然而,寻找生命的真正突破不止于技术,而是在想象和概念的层面上提供新视角,重塑人类对自身未来的理解。要深入理解这些观念,我们首先必须探讨天体生物学理论是怎样指导科学家在系外行星上寻找生命。
寻找外星生命,也就是寻找共同演化的生物圈。该基本理念,直接源自洛夫洛克那天在喷气推进实验室的洞见。银河系中任何拥有足够活跃的生物圈的行星,都会通过其生物活动改变行星环境,并在星际范围内留下可检测的“生物印迹”(biosignatures)。
例如,大气中的氧气和甲烷的共存就是一个典型的生物印迹。由于它们之间的化学反应,这两种气体本应迅速消失。如果在某颗系外行星的大气层中发现检测到它们共存的证据,便意味着该行星上可能存在一个强大的生物圈,持续向环境中补充这些气体。因此,天文学家的目标是通过观察遥远系外行星的光谱,寻找诸如氧气和甲烷等成分的光谱特征。
正如生物圈的存在会留下生物印迹,“技术圈”(technosphere)也会留下其独特的“技术印迹”(technosignatures)。技术圈这个概念,是地质学家彼得·哈夫(Peter Haff)最早提出的。技术圈是“建造技术的物种”在行星尺度上的活动,它包括所有形式的能源获取、运输和生产网络,以及遍布全球的各种机器。
如果技术圈的活动足够强大,它也会在来系外行星的光谱中留下印迹,即“技术印迹”。像氯氟烃(CFCs)之类的工业化合物就是技术印迹的一个例子,我和同事们在NASA的第一个此类项目中对其做过大量研究。我们发现,在跨越星际距离的系外行星上,我们甚至可以探测到当前地球水平的氯氟烃排放。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气体可能并非污染,而是为加热一颗行星,使之“变得”宜居而故意排放的。这是可能的,因为氯氟烃是强效温室气体,可以被注入大气层以提高行星温度,从而使其变得适合生命居住。大规模使用太阳能收集器产生的反射光,也可能是一种技术印迹。
对生物印迹和技术印迹的搜寻,代表了天文学的前沿,也将定义二十一世纪天体生物学的大部分工作。科学家们对此充满兴奋,首次就如何寻找生命达成共识,包括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和建造这些工具的资金。
许多非科学家也同样兴奋不已。千百年来,人类始终在思考“宇宙中是否只有我们?”这一问题。在我们即将找到答案的同时,公众也在高度关注。这种全球性关注,将成为推动行星观作为一种文化宇宙观发展的重要力量。
“‘行星观’是一种新的‘宇宙观’——作为全球现代性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秩序的替代方案而出现。”
行星、行星智慧与系外盖亚
那么,在行星观中出现的天体生物学的关键特征是什么?它所揭示的新宇宙观设计,将如何像唯物主义和机械论世界观在哥白尼/牛顿革命中那样具有变革性?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从这些碎片中组合出行星观的整体思想架构。
洛夫洛克指出——生物圈会从根本上重塑行星——使共同演化成为理解任何宜居行星历史的核心。随之而来的问题,既与技术圈(如我们最近建立的那个)相关,也和地球生物圈十亿年的历史相关。共同演化是怎样建立的?生命是怎样构建出那些能够对行星产生如此强大影响的反馈网?
这些问题又把我们带回洛夫洛克和马古利斯在大约半个世纪前,最初提出盖亚理论时提到的那些问题。盖亚理论早期受到的批评之一,就是认为它看起来是在暗示,生物圈有某种目的或目标。这可能吗?如果生物圈可以改变行星的演化,使之保持宜居性,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说它有某种目的?生物圈在某种程度上是否可以被认为对其所在行星的状态有所“知”?与之相比,技术圈的目标是明确的,由创造它的智慧生物所赋予的利益和需求驱动。那么,当一个具有明确目的性的物种所建立的技术圈叠加在生物圈之上时,会发生什么?
从这些问题出发,我们可以引入行星性宇宙观的一个核心概念:“行星智慧”(Planetary Intelligence)。该观点认为,生物圈和技术圈与行星之间形成的庞大而复杂的反馈网可以用信息和意义的概念描述。要理解行星智慧可能意味着什么,首先得考察盖亚理论是怎样在天体生物学中得到明确表达的。
2016年,电影导演阿迪提亚·乔普拉(Aditya Chopra)和天文学家查理·兰维沃(Charles Lineweaver)引入系外盖亚(ExoGaia)概念。他们认为,要使行星在数十亿年里保持宜居,生命的存在是必要条件。一旦生命出现,生物圈就必须建立洛夫洛克和马古利斯描述的反馈机制。否则,随着时间推移,行星不断变化的天文环境将使其无法支持未来的生物演化。宿主星体输出能量的稳定增长,就是行星天文环境可能发生危险变化的一个例子。随着恒星逐渐变亮,行星的温度将升高,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最终将导致海洋蒸发殆尽,所有生命走向灭绝。
因此,根据系外盖亚理论,所有长期存在的生物圈,必定都演化出可以改变行星演化的复杂反馈网络。行星科学家阿文·尼科尔森(Arwen Nicholson)和她的同事们进一步发展这一概念。他们展示了生物圈何以演化出化学反应网络,即便在恒星变亮的情况下,也能把行星温度维持在宜居范围内。
因此,行星生物圈必须经历从“未成熟”状态到“半盖娅”(semi-Gaian)成熟状态的转变。在未成熟状态下,生物圈的反馈能力较弱,对行星环境的影响有限。而在成熟生物圈中,生命网络完全重塑了行星演化的可能路径,使生物圈得以主动塑造行星的未来演化进程。这正是“行星智慧”涌现的可能性之处。
“这就是现在我们为何必须关注那场正在进行的、理解宇宙中的生命上的革命——我们将称之为‘天体生物学转向’。”
自创生、分布式认知和复杂系统的认知能力
把整个世界和任何种类的智慧概念联系起来,有人可能会对这个想法感到震惊。当天体生物学家戴维·葛林斯波恩(David Grinspoon)、萨拉·沃克(Sara Walker)和我在2022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们是在广义上使用“智慧”这个词的,即把它理解为认知、“知道”和回应。作为桥梁,它使我们可以把关于行星智慧的想法和行星观关联起来。我们是通过把行星智慧的概念基础置入快速发展的、研究复杂性科学和复杂适应系统的科学,从而建立起这一本质联系的。
复杂系统有别于只是“配置方式复杂”的物质配置(如缠起来的线球)。复杂适应系统是由嵌套的层级子系统组成。以动物为例,动物由器官构成,器官由细胞构成,细胞又由蛋白质构成,以此类推直至下降到“基本单位”,即其原子和成分。通过这些组织的层次结构,复杂系统表现出其最重要的特征:它们是自组织的。它们能够自主创造和维持自身持续存在所必需的各种过程和产物。
可这些过程和产物也正是它们自生产的手段。一个具体的例子是细胞膜。细胞膜的存在,使细胞得以持续存在。它让细胞需要的化学物质进入细胞,同时把有害的化合物拒之膜外。而正是这些选择性渗透的特性,使得细胞膜本身得以被生成和维持。换句话说,细胞膜的存在依赖于细胞膜的功能。
这种自组织如此重要,智利生物学家洪贝尔托·梅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和弗朗西斯克·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专门给它起了一个名字:自创生。自创生,即自我创造和自我维持。正是这个关键的怪圈,使生命成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并使复杂系统截然不同于此前科学所试图理解的一切事物。
自创生和自组织也是人们自然而然从目的论角度描述复杂适应系统的原因。它们明显是有目标的。这些目标可能是原始的,就像在微生物的趋化过程中那样。在这个过程中,单细胞有机体识别营养梯度并向上移动。在这种情况下,目的只是存续,继续活下去。但复杂适应系统的目标也可以高度结构化,就像在致力于让医保覆盖更多公民的社会中那样。要点在于,从复杂适应系统的角度来看,生命从来不会盲目与环境碰撞。相反,这样的系统可被有效描述为“能动体”(agents),以某种程度的“认知”来感知和调整自身及其环境。
对我们关心的问题来说,最重要的是,复杂性科学大大拓展了我们对认知和知道于何处发生、如何发生的理解。对“液态大脑”研究来说尤其如此。所谓液态大脑,指的是像白蚁、蚂蚁和蜜蜂那样集体形成的智慧。人们很早就认识到,这些“真社会性”(eusocial)物种表现出扩布式认知的属性,这也是为什么E. O. 威尔逊(E. O. Wilson)把蚁群和蜂巢称为“超级有机体”。近期研究也表明,甚至在微生物群落中,通过细菌的“群体感应”(quorum sensing),也存在扩布式认知的某些特征。比如,个体微生物之间传递的化学信号可以让群落采取集体行动抵御掠食者。
此外,目前还有研究致力于弄清楚连接树根的地下真菌网络是怎样生成扩布式合作的。初步研究指出,这些网络使树能够集体行动,在广阔的森林中,把营养从健康的区域输送到遥远的不健康区域。尽管此类研究尚存争议,但它也表明在讨论这个主题时涉及的范围有多广。
因此,集体智慧能走多远?它能在多大规模上起作用?生物圈可能是一个展示出某种形式的扩布式认知的集体吗?
一旦我们把作为复杂系统的生命的所有这些特征和生物圈行星级的功能结合起来,行星智慧的可能性便出现了。地球上的生命至少始于三十五亿年前的太古宙。起初,它是一个不成熟的生物圈。这意味着,地上的生命太过于稀薄,无法对地圈产生强反馈。它还不能改变像大气化学那样的行星特征。不过,在随后大约十亿年里,生物圈就成长到了能向海洋、大气和陆地大量输送氧气的程度。可以说,当时一个成熟生物圈正在涌现。
一旦生命演化为由微生物群落组成的行星网络——它们集体地对地圈的其他部分施加压力——我们就可以认为,那个集体有了一定程度的认知能力。简言之,组成生物圈的集体会使用信息。而复杂适应系统中能动性(agency)的标志,就是以存储、复制、传输和处理方式使用信息。如此,我们可以说,在差不多三十亿年的时间里,地球上出现了行星智慧,或者说,任何一颗形成这种成熟生物圈的行星上都会出现行星智慧。
生物圈实现了自组织和自创生,也意味着已达到成熟阶段。通过复杂的生命网络,成熟生物圈积极地维持而非削弱自身存在所需的条件。信息在这些有生命的网络中流动,并被其使用,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把成熟生物圈当作一个集体,这个集体掌握关于自身状态的知识,并对该状态及环境的变化做出回应。成熟生物圈有所“知”,并用以维持自己横亘地质时期的行星尺度上的宜居性。
注意,这种智慧并不依赖于意识或有意识的控制。行星智慧是一种自组织的适应过程,能够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运作。然而,一旦意识出现,系统的复杂性就会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我们也可以把行星智慧应用于技术圈,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新的行星宇宙观的全部潜力。
“我们首次就如何寻找生命达成共识,包括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和建造这些工具的资金。”
成熟技术圈与行星智慧重现
在完成关于生物圈的研究后,维尔纳茨基最终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理论。他认为,一旦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以技术能力形式出现的“文化能量”又创造了另一组可能性。这个新的圈层被称为智慧圈(noosphere)——希腊语“noos”意即“思想”。
大多数人熟悉智慧圈的另一个版本,即耶稣会神父、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更具宗教性的“世界灵魂”。维尔纳茨基的版本,则更具科学实证基础。
对维尔纳茨基而言,智慧圈是通过技术系统网络展现的人类能动性的总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技术圈。维尔纳茨基敏锐预见到,未来技术圈收集能量的能力合起来,会对行星产生广泛影响,就像生物圈作用于地圈那样。但他未能预见到,技术圈会怎样破坏它赖以存在的地球系统。而我们现在,已经能够清晰看到这一点。
我们不但能够通过气候变化直接测量技术圈对行星地球的影响,还能从更宽广的行星智慧视角看到这一影响。此种天体生物学视角使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建造的技术圈依然极其不成熟。它尚未发展出为确保自身生存所需的集体的、扩布式的认知能力,即它还没有获得行星智慧。
本质上说,技术圈是文明的集体工程。如今,这个工程消耗了生物圈通过光合作用采集的能量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这种能量采集对地球系统的影响是破坏性的。气候变化只代表了我们涌现中的技术圈给行星带来的后果之一。从运输像磷那样的关键营养物质到增加海洋的酸度,技术圈的活动正在跨越多个边界,威胁着支撑其生存的生物圈的稳定性。
数十年来,我们知道有气候变化这回事,也知道我们离行星的那些界限越来越近了。固然知之,我们的全球治理和控制体系却一直未能有效调整技术圈发展方向,避免其向崩溃冲刺。
这一全球行动上的失败具有启发意义。那些国际控制、治理、生产和金融系统本身,就是技术圈的一部分。它们构成了技术圈的“信息架构”。如上所述,复杂性科学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对复杂适应系统来说,信息的作用同物质和能量一样重要。
生物圈既由实实在在的树木构成,也由使森林成为可能的基因的、代谢的和生态系统规模的信息流构成。同样,技术圈既由像集装箱船那样实实在在的技术构成,也由支撑其建设和使用的信息组织——企业政策、国际条约和非政府组织协议构成。技术圈既关乎控制的信息组织,又关乎被控制之物。
有了这个认识,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技术圈从根本上的不成熟含义在于——它正在削弱维持自身存在所需的条件。借鉴成熟生物圈的愿景,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为避免气候变化及其引发和加剧的多重危机,我们必须创造什么。
从天体生物学的长远视角来看,这一观点变得尤为清晰。任何技术圈,为了在一个星球上长存,而非仅仅短暂存在几个世纪,都必须通过表现出一种新的自组织形式而变得成熟。如果要持续存在超过半个地质时间尺度(几千年)的时间,它就必须具备自创造和自维持能力。因此,一个成熟的技术圈将是自创生的。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它必须复现其所依赖的生物圈在数十亿年前所建立特性,即行星智慧。这是技术圈像生物圈那样得以跨越时间尺度经久繁荣的唯一方式。
成熟技术印迹的独特性和新颖性(天体生物科学为这些印迹而兴奋不已,也在于此)在于,这些印迹的出现带有明确的目的论。当一个物种首次建构一个技术圈,即使是不成熟的技术圈时,它也就变成了行星物种。然而,真正的转变发生在该物种意识到自身在建立这种覆盖整个行星的技术系统中所拥有的力量和影响。任何能够将其技术圈发展至成熟阶段的物种,都会在其与行星系统的耦合新形式中,融入意图和目标。通过以这种方式明确体现目的论和意义,成熟的技术印迹代表了盖亚潜能的完全实现——即一颗行星自我觉醒。
“生物圈可能是一个展示出某种形式的扩布式认知的集体吗?”
作为新宇宙观的行星观
哥白尼革命改变了人类看待自己在宇宙中位置的视角。很快,人们意识到,支撑这一天体重组的牛顿科学也可以成为获取物质财富和权力的驱动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科学成为塑造全新世界体系的想象基础。
不过,这个新世界死了。它是一个完全唯物主义、机械论和还原论的宇宙。生命被还原为“仅仅是”分子机器。生命系统的绵延奇异性及其能动性、自主性甚至感觉(即体验)能力,也被视为仅仅是亚原子粒子运动的附带现象。生命本身被置于次要地位。在这种机械论科学本体论的等级结构中,与原子或时空相比,生命并不具有根本重要性。
在科学获得权力的同时,一切声称为之代言的哲学也获得了权力。不足为奇,十八和十九世纪蓬勃发展的工业政治经济体系,都吸纳了生命和地球的唯物主义机械论视角。
无论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都依赖于此种宇宙观。在这种视角下,山川和田野都可通过还原来看待,都被看作“不过是”可供开采或耕种的资源。地球作为一个活生生的行星被忽视,“环境”只是工业废料的倾倒场。
在这种行星性盲区的影响下,现有政治经济长期拒绝承认气候变化及其后果也不足为怪。要理解全球变暖和人类活动的行星影响,需要摆脱“经济人”(homo-economicus)的狭隘视角,同时也需要把生命视为不只是由组织和骨骼构成的机器。
回顾过去的五个世纪可以看到,出自哥白尼转向的宇宙观存在多么严重的缺陷。我要指出的是,承认这个缺陷,不等于拒绝现代科学,或否认其对人类的重要贡献。可以在尊重科学的同时依然看到,我们今天面临的诸多危机,正是源于一种声称为科学代言的世界观、形而上学和宇宙观。但科学本身并不是形而上学也不是政治哲学。科学是一种进入与自然对话的强有力方法。科学也不是静止不变的。
天体生物学和复杂性科学是那场对话中的新线索,它们揭示了关于宇宙的新洞见。对行星观涌现至关重要的是,它们为行星与生命提供了一种摆脱旧宇宙观死寂世界的全新视角。
首先,科学界逐渐认识到,在由空气、液态水、冰和岩石构成的耦合地球系统中,作为生物圈的生命扮演着同等重要的角色。这是盖亚理论的主要成就,并在后来发展为地球系统科学。
一旦气候变化得到承认,地球系统思想上就又多了技术圈这个维度。关于生命、行星及其共同演化的问题,突然有了新的紧迫性。然后,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对系外行星的发现,把天体生物学带到了天文科学的前沿。成千上万颗星球可供探索。
于是,一个依赖于生物圈及其改变行星力量的盖亚理论,旨在识别生物印迹的领域出现了。科学家们用这个力量来想象,任何星系的任何世界上的任何一种生命都可能创造出其自身存在的、可被探测的印迹。
最终,人们也对外星技术圈提出了相同的问题。研究系外星球技术物种重塑其行星环境、并在星际尺度上留下可探测技术印迹,也变成一个方兴未艾的国际研究项目。
这些新发现和新研究项目都要求我们以不同方式认识生命及其在宇宙中的位置。在这一点上,地球系统科学是明确的:必须在系统的层面上考察生命和行星。换言之,有生命的行星是认知上的整体。
为认识地球(或任何行星)系统,对一些问题进行还原可能是有用的。但在这种星球和生命观中,没有作为一种总体化哲学的还原论的位置。正是在这里,我们第一次在摆脱哥白尼旧宇宙观的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进一步说,复杂性科学是赋予天体生物学中“生物”概念核心动力的学科,它要求把生命视为一种涌现现象(emergent phenomenon)。正如理论生物学家斯图亚特·考夫曼(Stuart Kauffman)所言,生命是“基于物理学却又超越物理学”的。复杂性科学的核心原则是,涌现系统不只是其部分的总和,而是具有创造力、创新力,并充满不可预测的惊喜。
天体生物学的视角就是这样,在不依赖任何形式的活力论的情况下告别唯物主义。有生命的系统并不仅仅是“纯粹的”物质,它们是宇宙中唯一使用信息的物理系统。在实现自创生自组织的同时,生命也把信息的语义维度变成其自身组织的核心运作机制。意义与物质同样重要。这也是在摆脱哥白尼转向之宇宙观的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从把生命看作涌现的复杂适应系统的新观点来看,一种对生命和行星的更宽泛的整合性理解也变得可能。地球,或者说任何被生物圈和技术圈改造了的世界,都是在行星尺度上演化的新陈代谢塑造出来的。最重要的是,一旦共同演化开始,能量、物质和信息在其中的流动便赋予该行星具备行星智慧的潜力。
成熟的生物圈是有能力引导流入的恒星能量,以维持自身可持续性的系统。它们形成单一的自维持系统,无论是出于科学研究还是建设长期可持续文化的目的,我们都必须这样看待它们。这也包括对政治经济学的设计,现在,我们必须把它看作一种新形式的行星尺度的新陈代谢。
因此,对生命和行星的天体生物学视角,促成了天体生物学转向。在它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人类关注的问题做一次新的排序,因为它提供了能够直接塑造一个新世界体系之建构的命令、处方和目的论。技术圈出自生物圈,生物圈又出自无生命的地圈。行星自有其运行法则,任何物种若妄图凭借自身创造超越这些法则,忽视其赖以生存的行星,终将自取灭亡。
就像维尔纳茨基提醒我们的那样,“生物圈收集并重新分配太阳能,最终将其转化为能在地球上做功的自由能”。这是天体生物学转向的关键所在。它也是新的行星观宇宙观的终极基础,它不仅适用于地球上的人类,也适用于宇宙中所有可能存在生命的行星。
因此,我们的目的必定是利用这些能量,推动技术圈的成熟,使之与生物圈和其他地圈保持和谐一致。鉴于我们所知的生物圈自己的历史,寻求技术圈的成熟和行星级智慧,是人类实现长期繁荣的唯一道路。这也是通向天体生物学家戴维·葛林斯波恩所说的智慧世(Sapiezoic Eon)或者说智慧时代的唯一轨道。
“成熟的生物圈有所‘知’,并用其知维持自己在地质时期内的行星级的生存能力。”
行星观愿景与行星性愿景
如果一种全新的行星性宇宙观涌现并扎根于人类社会,世界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它将催生何种文化组织和政治经济秩序?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因为这种涌现本质上是开放、创造和演化的。
行星性新秩序的形成方式,将决定其最终形态。而且,要见证其全面实现,或许需要超越一代人的时间。想象一名十六世纪晚期的商人或学者。关于哥白尼的科学如何最终深刻影响市场资本主义,他们能勾勒出哪怕是最粗略的轮廓吗?
不过我们至少可以从天体生物学视角及其复杂性科学基础,预见一些行星性宇宙观的潜在影响。尤其值得探讨的是,行星性宇宙观将如何自组织?
成熟技术圈是行星观的终极目的。它将是行星智慧的再涌现,因为它遵循在它之前的成熟生物圈的组织设计。但这种技术圈会怎样组织它的物质结构、能量结构和信息结构?本质的创新在于,未来的技术圈将构建一套不可被削弱的自维持能力。换言之,它的系统设计将使破坏其自维持能力变得不可能,甚至不可想象。
想想当前技术圈的组织及其所有的治理、金融和生产网络。如果我想去银行贷款造核武器,我很快就会发现,这个提议行不通。贷款员都不需要查任何规章制度,因为把全球金融用于此目的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同理,我们也可以想象在行星观塑造的未来,申请贷款来建燃煤发电厂也同样会是不可想象的。每个人都会知道燃煤发电厂对生物圈的新陈代谢产生的影响。深感震惊的银行经理会告诉我:“你当然不能获得资金来建这样的东西。”
因此,行星观意味着承认文化的组织始终嵌套在行星代谢的反馈环之中。目前,随着行星观的逐步形成,这也意味着,任何不把“行星”这个词纳入其意图的新政治经济理论都失去了头绪。
把行星观植根于复杂性科学的生命观也使我们可以想象,未来申请贷款用于工业化肉类生产也同样不可想象。当然,素食主义仍将是一种个人选择。但随着我们的生命观从机器隐喻滑向对作为一种基本衡量标准的能动性的承认,我们把动物仅仅视为工业规模开发的经济资源看待的意愿也会发生变化。
即便行星智慧只被看作一个隐喻或指导原则,它依然意味着对生物圈内多种形式的感知能力的承认。正如《关于动物意识的纽约宣言》展示的那样,这种承认已经在科学中发生了。该声明由一个多元的学者群体共同提出,他们主张,当前的科学研究表明,动物普遍具有意识是一种切合实际的可能性。这一宣言也引发了随之而来的伦理影响的严肃讨论。
将新世界体系根植于行星性宇宙观,也将引导我们进入全新的领域,重新审视我们如何讲述关于知识及其持有者的故事。奇异的“万物至理”是旧有的唯物主义、机械论宇宙观提出的要求。行星观不需要这种从单一视角来理解的总体化叙事。相反,行星性宇宙观强调知识的多元性,因为它承认,任何现象都可以从多个视角进行理解和诠释。
这种看法直接融入了复杂性科学,后者本身就依赖多种研究焦点和方法范式。这些范式中的每一个,都能围绕同一个问题讲述不同类型的故事。正如复杂性理论家戴维·克拉考尔(David Krakauer)所写的:“复杂性科学应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范式的复数性不但有效用,而且不可避免。”
因此,在行星观中,没有哪种文化或文化史能建立凌驾于他者之上的霸权。这样,它也就能够摆脱哲学家和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认为的,先前生态运动在政治上无效的根源。行星观拥抱生物圈和技术圈在多种视角和尺度上的运作方式,确保地方性不会被全球性所吞没。总有地方供人立足、支持和捍卫。总有附着于具体生命和文化的家园和土地。行星观从来不是祛身的。
正如莎士比亚所言,时机就是一切。天体生物科学获取其他世界上生命问题相关数据的时间尺度将以十年为单位。这将是一个在二十一世纪展开的故事。宜居世界天文台(NASA搜寻生命的未来旗舰天文台),预计将于四五十年代发射。它在接下来几十年里做出的观测将提供关于群星间是否存在生命,以及这些生命存在于何处的最好回答。
这一时机也意味着,我们关于宇宙中生命的首批答案,将在气候危机及其引发的更广泛的多重危机达到高潮时到来。新的行星性宇宙观可能也将于那时兴起和立足。
当然,未来并无定数。人类的未来可能会被各种更黑暗的前景所束缚,并持续一个世纪以上。但就像哥白尼革命及其后续发展所示,行星观始于我们对行星的新愿景。而我们已经获得了这一视角的初步洞见。
如此这般,故事、逻辑和设计交织而成的行星观“生命纤维”已在生长。在威胁我们的烈焰的驱动下,一个趋向一种新的人类自我构想和自组织的势头正在积蓄。如果可以给这个势头添砖加瓦,我们会自己发现正处在地球及其孩子们告别青春期、走向成熟的关键时刻。
译者:王立秋,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