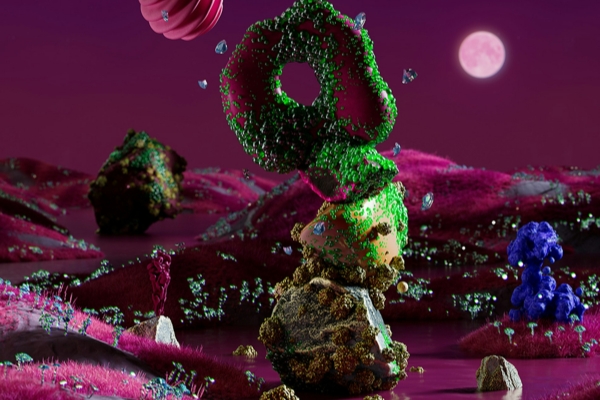“都会好的,都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诺里奇的朱利安
“对谁来说好了?对谁来说好了?对谁来说都没好。”——钦努阿·阿契贝《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中依博族在葬礼上的挽歌
20世纪40年代中期,美国官员约翰·科利尔(John Collier)审视了西方世界道德和生态遭到的破坏并得出一个悲观的宣判。他在1947年出版的《美洲印第安人》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我们的种族,伴随着所有已经失去与尚未失去的价值,正在自我毁灭的边缘徘徊。”
在两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大屠杀和原子浩劫之后,科利尔的论断并不独特,甚至很可能都算不上不同寻常。该论断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尤其考虑到它出自一位美国公务员之口,科利尔将这种种族的自我毁灭归因于个人主义、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法则……被认为是人类生活的法则……[即便]它对社会、传统、伦理价值和美学价值、家庭和社区生活,甚至是地球本身的自然资源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就其所处的时代和场所而言,同样不同寻常的,还有科利尔提出的方案。他认为,消除工业资本主义各种掠夺的解药,是使非原住民的西方人最终认识到,他们必须效仿纳瓦霍人、霍皮人和其他部落民族,培养“对生命之网和自石器时代之前起就被美洲印第安人当作中心圣火来照料的大地……的热爱和尊重”。
值得注意的是,科利尔并非仅仅以“高贵的野蛮人”的陈词滥调随意提出这一观点,相反,他是一位敏锐的思想家、才华横溢的作家,同时也是位高权重的行动者。作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时期(1933年至1945年)印第安事务署的专员和“印第安新政”的主要作者,他几乎凭一己之力,逆转了美国对原住民同化的政策,结束了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宗教迫害,并使众多部落民族得以恢复自治。
科利尔基于对那些与行星地球和谐共处的文化的深刻理解,形成了他的核心信念:如果西方世界能够“重新获得”这种源于集体生活和神圣化自然的“力量”,那么,“地球的自然资源和生命之网就不会在20世纪内遭到不可挽回的浪费,这就是现在的前景”。他把这种对大地的敬畏的恢复称作“长远希望”,并强调,“这是我们唯一的长远希望。”
差不多同一时间,大西洋彼岸的J. R. R. 托尔金(J. R. R. Tolkien)也对生态灾难的步步逼近感到深切的忧虑。在其代表作《精灵宝钻》和《魔戒》中,托尔金谴责了工业化对行星地球的污染和人与自然的日益疏离。在他所创造的中土世界中,反派角色无一例外都是憎恨自然和“树木杀手”,都是满脑子“金属与车轮”、“只在用得上的时候,才会去关心生长的事物”的权势之流。他和科利尔一样,对这个用科利尔的话来说“以工业革命的核心价值为尊,认为其关于人性的假设……完全正确”的世界感到悲哀。
托尔金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我们应该做什么,更准确地说,是对我们可以做什么的看法。科利尔抱有“长远希望”,认为西方人或许最终能够拒斥基督教—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回归美洲原住民所持有的万物有灵论的社会信仰。托尔金则认为,我们应该与灭世者进行一场英勇、永无止境且最终徒劳无功的战斗。
他将这场持续战斗称为“长久失败”,并让中土世界的不朽精灵在“世界时代”中与之抗争,努力延缓他们无法阻止的命运:权欲的力量终会肆虐,生命世界的原始天赋终将被彻底扑灭。
在科利尔和托尔金提出他们的构想大约80年后,如何以最佳的方式应对这个已知半已知(known and semi-known)世界的毁灭性破坏,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议题。在这场讨论中,“希望”一词频繁出现,甚至被视为危机应对辩论的主要修辞模式。例如,在环保主义者戴维·铃木(David Suzuki)和科学家莱斯利·施彭泽尔(Leslie Sponsel)的大量著作中,就呈现了科利尔通过借鉴原住民的精神实施改革并恢复行星地球的长远希望。
短期的、号召行动式的希望更加频繁地出现,例如在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古道尔(Jane Goodall)、活动家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和政治学家托马斯·霍默-迪克森(Thomas Homer-Dixon)的著作中。与此同时,失败则通常以牛鬼蛇神(bogeyman)的形象出现,是我们任由希望落空后未来会变成的那个吓人的“否则”;除此之外,失败在大多数深思熟虑的讨论中几乎都被排除在外。
可以说,这个方子没用。正如人们所言,众多事件压倒了我们;末日的迹象正不断堆叠。然而,尽管有成千上万的文章、书籍和媒体片段在为我们时代自封的毕业生代表发声,西方和西方化世界的民众却依然不为所动、不知所措并顽固地感到无望。
事实证明,长期以来人们在环保运动中以各种扭曲、不诚实的方式使用的那些传统的希望修辞,并不适合我们当前的全方位危机。尽管科利尔那个远大愿景更具吸引力,但在一个未来始终逐渐萎缩的时代,它显然失去了立足之地。
显然,我们需要改变传递信息的方式。戴维·华莱士-威尔斯(David Wallace-Wells)在其气候变化书籍《不宜居的地球》(The Uninhabitable Earth)中指出,传递气候信息的方式之所以会一直停留在默认的希望修辞模式,是因为我们缺乏适应如此规模的灾难的叙事框架,可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可以认为,托尔金的“长久失败”故事,就是为我们的时代量身打造的修辞工具。这个故事涵盖了从宇宙到有机体的时间尺度,它把时间深处的灾变(the deep-time catacleysms)大规模地、明确地显示在我们面前。
在描述与一系列形形色色对手展开的人类级(human-level)战斗的时候,托尔金的故事给我们提供了应对他们的方式:激发英雄精神而非寄托于希望,唤起勇气而非追求安慰。同样重要的是,让人们参与到故事中,而不是用信息来吓唬他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从这个更加冷酷的真相中汲取灵感:我们可能没有能力阻止终结,可如果愿意与长久失败斗争,也许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结局。
希望修辞的失败
我们面前的哪些证据表明,希望修辞失败了呢?稍微归拢一下就会发现,几乎所有证据都指向这一点。首先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希望修辞使我们可以淡化气候危机和生态危机的影响,从而在正在发生的现实和广为人知的事情之间创造一个荒谬而重大的“紧迫性差距”(an urgency gap of mock-epic proportions)。
那些以“精灵的生命尺度”观察地球的气候科学家和历史生态学家报告说,我们逐渐意识到,我们被拉入了一场进行中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在意识到问题之前就丧失了大部分阵地,而防止华莱士-威尔斯所说的不宜居星球的“零度地球”场景出现的唯一机会,在于打一场绝望的顽抗之战。
任何忠实呈现他们对不远未来的憧憬,都必然带有某种末世特质。就像华莱士-威尔斯说的那样,后工业化时代气温上升2度——现在这已被认为是最好的情况了——带来的后果包括,“城市被洪水淹没,干旱和热浪成灾,行星地球每天都受飓风和季风重创”。这个场景还忽略了生物多样性丧失可能带来的更具灾难性的影响,后者被末日时钟管理者列为与气候变化和核战争同级别的行星级威胁。
在传递这场“(死亡)五百万人级”大火的新闻的时候,以希望为中心的环保作家和向大众普及科学数据的科学作家使用了魔法思维的核心三段论——我们应该,所以必须;我们必须,所以可以;我们可以,所以将会——来说一堆“应该是”的囫囵话,几乎不足以促使任何人脱掉睡袍采取行动。
比如,铃木在《神圣的平衡》(The Sacred Balance)中写道:“我们还有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采取强有力行动来促进变革;只要团结起来,我们就能重获那种古老而持续的和谐,让人类的需要和所有我们在星球上的同伴的需求与大地神圣的自我更新过程保持平衡。”
被誉为“首席希望官”的古道尔也在《希望之书》(The Book of Hope)中写道:“如果每个人……都开始思考我们行为的后果……如果我们都开始问[某件物品的]生产会不会损害环境……那么,数十亿这样的伦理选择将推动我们走向我们需要的世界。”
政治学家霍默-迪克森在《指挥希望》(Commanding Hope)中写道:“我们需要一起主动从多样的视角出发,创造一个关于积极未来的共享故事……[并]全面调动我们非凡的人类能动性,去实现那样的未来。”
这些推理的首要问题,不在于它们依赖教科书式的循环论证:“如果做了我们为拯救世界需要做的一切,我们就能拯救世界!”它们的问题甚至不在于,相关各方采取及时、充分行动的可能性,在最宽容的情况下也只能是“非零”。问题在于,它们一厢情愿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就算所有人都立刻采取行动,情况也会继续恶化,只是(也许)速度没那么快。
这就是令人遗憾的真相。根据许多科学家的预测,地球的全球平均温度有可能上升2.5摄氏度。未来五十年,由于气候变化,据估算多达六百万种动植物可能会灭绝。
事实是,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既定事实。因此,一切希望的信息,至少在接下来“半无限”轮回中,只要它们描述的不止是一种微不足道的胜利,都只是谎言而已。当前正被造成的破坏代表着我们不可挽回过去的行动后果,就像一封我们写给自己、却迟迟没有寄出的噩耗信。如同环境记者阿诺·科佩基(Arno Kopecky)在《环保主义者的困境》(The Environmentalist’s Dilemma)一书所写:我们“正活在借来的时间里。最糟的还在后头”。
希望主义者拒绝承认我们危机的前定性,即便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的核心所在,也是使我们陷入绝望无法动弹的主要原因。这个拒绝反映了环保主义修辞中的一个长期传统,即对系统层面的因果关系和系统层面的现实(看似离散的后果)视而不见。
自20世纪70年代现代环保运动兴起以来,老派的活动家就一直依赖一种伴随评判性预期的“行动—英雄的希望”,并以一种基于先例的方式用这种希望来暗示,“我们阻止了那种滥伐,希望[言下之意:期望]你们能阻止这次滥伐”“我们那一代人禁止了DDT,希望并且期望你们这一代人能禁止一次性塑料”“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核威胁,你们也不应该放弃逆转臭氧层变薄(这件事情)的希望”。
这个“对号入座”的传统忽视了这样一个我们不便接受的事实,即消费主义资本主义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生成越来越大规模的危机。它在本质上一直是不诚实的。不过,活动家们可能会认为,这种方式是针对具有“节点化”的历史观并排斥系统性改革的西方受众最有效的信息传递方式。
不过,在系统性后果全面暴露的情况下,这种假装已变得荒唐可笑。更重要的是,它在修辞上也说不过去了。首先,在劝我们通过记住过去的胜利来保持振作的同时,预期我们将因此而振作起来的自我投入救世行动,这样的做法注定会引发怨恨。怨恨也确实在不断产生,尤其是在基本上被指定来承担大部分工作的年轻人那里。这种情况只会加剧希望意图克服的那种不作为。
伊莎贝尔·德鲁里(Isabel Drury)在为“恐惧一代”(Gen Dread)电子报撰文时指出在上一代人说“年轻一代对气候危机的奉献让我充满希望”时,她听到的却是:“对,我知道我们把行星地球搞的一团糟……可现在我无能为力。这是你们的问题。祝好运!”
使得强迫的希望更显冒犯的,是这样一种错误的等同,比如说,把拯救一片雨林中的一小部分免于砍伐,等同于把整个世界从多方面的气候崩溃中拯救出来。这些作家还不如说:“多年前,我从窗台上救了一只苍蝇。现在,你可以用相同的技巧,阻止兴登堡号(Hindeburg)坠毁。”
我们当前诸多危机的空前性质在程度和种类上都不一样,显而易见,对此有很多人做出了评论。然而,希望派作家们依然把自己的论证建立在不适用的参考资料之上。比如说,不少人引用政治学家埃里卡·切诺维斯(Erica Chenoweth)的理论,声称只要有3.5%的人参与公民非暴力抗争运动,就足以令这场运动成功。在《环保主义者的困境》中,科佩基在回应这个观点的时候评论说:“据我所知,切诺维斯的所有案例研究都没有成功推翻人类的贪婪。”
那么,为什么这些老牌环保作家还在坚持希望修辞,甚至在它无法兑现承诺的希望成果时,仍不愿修正呢?这些成果不但违背了未来的可能性,也违背了当前的现实。
我们只能假设,这是路灯论证(streetlight argumentation)的一个大规模实例:就像人在路灯下找钥匙,不是因为钥匙掉在那里,而是因为那里最容易找。今天我们的演说家使用希望修辞,可能因为他们只知道这种修辞。
为转移人们对希望本质的注意——用艾米莉·狄金森的话来说,希望是“长羽毛的东西”,不应承担激励行动的角色,这些作家使用了另一种修辞谬误,即“说服性定义”:夸大对希望的性质和力量的描述。
例如,古道尔写道:“人们倾向于认为[希望]只是被动地异想天开:我希望某事发生但我不打算采取任何行动。这实际上与真正的希望相反,真正的希望是要求行动和介入的。”
在2023年接受气候记者斯特拉·莱万特西(Stella Levantesi)访谈的时候,作家兼活动家丽贝卡·索尔尼特也认为,希望不只是被动地异想天开:“希望对我来说”,她宣称,“只是认识到未来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当下决定的,因为这个现实,我们做的事情是重要的。”
如果你的字典与更加常规的标准一致,你就会发现动词“希望”的定义是“怀有对实现的期待来渴望;盼望;想要”。简言之,它的意思就是一种异想天开的愿望。
这些定义除了经过曲解之外,还夹杂着对希望过去取得的成就的夸大描述。比如,在《希望之书》中,古道尔的合作者道格拉斯·艾布拉姆斯(Douglas Abrams)讲述了一个旨在激励人心的故事。该故事源自大屠杀幸存者和心理学家伊迪斯·埃格尔(Edith Eger)。埃格尔提到,奥斯维辛一名年轻囚犯,靠着希望活了下来。这个希望基于一个传闻:圣诞节的时候她们就会被释放。当圣诞节到来,而解放没有如约而至的时候,这个少女马上就死了。作为希望战胜现实的描述,这个故事恰恰是一个有力的反面例子。但艾布拉姆斯选择性地从故事的中间部分而不是末尾得出结论,从而使故事服务于自己的修辞目的。
对于希望在这样的情境下起到的作用,曾是战俘的前越战海军中将吉姆·斯托克代尔(Jim Stockdale)做出了更加诚实的描述。在被问到什么样的人不能在越共集中营活下来的时候,他回答说:“哦,这很简单。乐观主义者活不下来。就是说到圣诞节我们就出去了的那些人。然后他们又说到独立日、到感恩节我们就出去了,之后又变成了圣诞节。……我想他们都死于心碎。”
更现实的是自然主义者本·加德(Ben Gadd)的推测,他在2007年的一次大学讲座中完全没有提到希望,而把生存归功于“视而不见的能力”。他指出,这个能力帮助“奥斯维辛的每个人,囚犯和毒气室的值班员”熬过了那些日子,在战争结束时,“双方都有令人惊讶的大量人员仍然活着”。
“长远希望”:消受不起的奢侈
如果说强调普通希望的信息传递方式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科利尔的长远希望——寄希望于西方和西方化世界通过效仿原住民的世界观来解决生态破坏的问题——则又引入了另一组问题。首先,实现这个愿景需要近乎无限的时间,而当前的行星危机则要求立即采取行动——更不用说需要时间旅行到生态史的早期节点。但这并没有阻止越来越多的作家吹捧“长远希望”的解决方案。
比如说,施彭泽尔在其著作《灵性生态学》(Spiritual Ecology)中写道:“世界早该听听原住民的智慧,以截然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贪婪的那些非人化、非神圣化执念的病态方式来做很多事情,否则那种病态会危及到整个行星家园。”
类似地,社区组织者丹尼斯·马丁内斯(Dennis Martinez)也赞扬“传统原住民作为另类现代性的现实意义”。生物学家和哲学家福尔维奥·马佐奇(Fulvio Mazzocchi)在2020年发表于《人类世评论》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需要汲取“原住民知识可能提供的洞见,[并]分析其与自然关系的原则,比如互惠和照料……[这些原则]源于深刻的团结和互联感,并强调回馈自然的重要性”。而长期倡导希望的铃木也写道:“我们需要一种研究原住民社群传统知识的新科学;对这种科学的探索已经开始。”
我们忍不住想和托尔金小说电影版里的萨鲁曼一起说:“你觉得我们还有什么时间?”
与那些对短期希望的设想类似,这些长远希望的愿景在时间上的自我放纵暴露了这样一个潜在问题,那就是:我们对危机的性质、规模和根源缺乏应有的认识。且不论在期限内实现精神启蒙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单单出于交易目的寻求精神启蒙这件事情本身就包含了内在矛盾。
问题的核心在于,形成以万物有灵信仰为核心的集体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即推翻基督教—工业—资本主义复合体或以别的方式使之消失,如今并不比在科利尔的时代更接近于成立。事实上,它反而与我们渐行渐远了。就算在科利尔看来,万物有灵论也是要取代这个复合体,而非与之共存——尽管他是带着一种颇为天真的情怀,认为我们可能会因为精神饥饿而被迫做出这一改变。
可以假设,如果集体主义的万物有灵论能与西方的世界观和经济体系共存,它早就与之共存了。更确切地说,它从一开始就不会停止与之共存。而且,世界上大多数既非原住民亦非犹太—基督教徒的人,也会继续在他们现有的宗教中表达对自然的敬畏,而不会觉得有必要接受原住民的信仰体系。毕竟,就像比较宗教学者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在她的书《神圣的自然》(Sacred Nature)中指出的,世界80亿人中有近一半的人信仰某种或多或少具有万物有灵论信仰体系的宗教,这些信仰体系的核心都是把自然神圣化: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儒教,概莫如是。
然而,这些强大信仰体系中把地球神圣化的元素并不能抵挡犹太—基督教和技术—工业资本主义的双重力量。正如历史学家小林恩·怀特(Lynn White, Jr.)在其1967年的论文《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The Historical Root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中指出的,犹太—基督教使我们与有生(和无生)世界的其他部分分离并假定我们高于后者;而技术—工业资本主义则利用这个精神上的脱离来谋取个体收益。这些西方强行推行、稳定输出的机械般的力量压倒了其他所有信仰体系,清空了可能抵抗它的自然崇拜元素。这还没完:2023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工业化的发展对地球上60%原住民持有的土地构成威胁,这一面积几乎是印度国土面积的七倍之多。
在我们找到一种像19世纪英国法官鲍恩勋爵(Lord Bowen)说的那样,在不义之人停止偷窃正义之人的保护伞体系之前,长远希望得以实现的胜算依然是巨大的负数。
事实上,长远希望通过大规模重新神圣化自然来拯救世界的许诺也有残忍之处。回归与自然更亲近的关系,可以说是人类内心和原始大脑中最深层次的希望之一。恋生(biophilia,爱恋生命),即人类与自然世界联系的倾向,也可以说是一种仅次于我们对社交需求的强大力量。
长远希望针对的是人性和人类精神的分裂;它悄悄告诉我们,我们还可以重新统一这二者。这个希望是西方人羡慕原住民的原因——虽然讽刺的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情感本身具有讽刺的非正义性——也是对环境破坏的悲痛之源。而这种情感也在变得愈发普遍。
可就在人们对这个希望的需要变得越发迫切的情况下,这个希望反而变得愈发不可实现。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在世界各地,按经济逻辑推行的城市化一直在加速,并且这个势头还在继续。到2050年,近70%的人类人口将在城市中生活,其中很多人别无选择。
环保主义者宣称,通过更多接触我们的“动物本性”,我们可以拯救自己和这个星球,这就如同一个有特权的种姓阶层(caste)发出的嘲讽:这个阶层可以在豪华的露营中享受森林浴,在其乡间别墅观鹿,或者花几个月时间在野外监测最新的生物学项目。
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即使在富裕国家,重新点燃内心的神圣之火不过是在截肢伤口上再添一道烧伤疤痕。从实际的角度来看,很难看到这样的改革会对隔壁的公寓楼起什么作用,更不用说对今天在城市中生活的全部44亿人会起什么作用了。
兜售这样的希望——我们会对人类采取一种不那么狂妄自大的看法,给行星地球更大的尊重,并以此为动力改变我们不可持续的(行事)方式——也是一种虚伪。即便这一愿景宣扬物种的谦虚(即宣扬人类这个物种要谦虚),但它所承载的预期,只有通过彻底的神性、通过否认我们物种的局限性才能实现。
正如华莱士-威尔斯和比尔·麦克基本(Bill Mackibben)到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和罗布·邓恩(Rob Dunn)等作家所指出的,人类一些看似根深蒂固的物种特征,用邓恩的话来说,“类似于法律的偏见”会妨碍我们有效应对诸如大规模物种灭绝、生态毁灭和气候变化此类的严峻形势。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倾向可能是旁观者冷漠,尤其是在责任分散的情况下,而这正是我们多重全球危机的核心所在。
科佩基也强调了这点,他写道:“我可以发誓不用内燃机,不吃肉,在屋顶上铺太阳能板,不碰塑料,余生每天种一百棵树,但这一切都不会让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更接近百万分之350,也无法缓解世界的生物多样性危机。只有当数亿人改变消费习惯的时候,这些问题才能得到改善。”
旁观者冷漠只是阻碍行动的心理障碍中近乎无穷无尽清单上的一项,这些障碍有很多是个体无法克服的。华莱士-威尔斯从一长串让行动变得困难的认知偏见清单中的字母A开头列举:锚定效应(anchoring)、模糊性效应(ambihuity effect)、人类中心思维(anthropocentric thinking)、自动化偏见(automation bias),接着继续列举到字母B,却甚至都没有触及可得性捷思法(availability heuristic)。可得性捷思法使我们的思维偏向最容易看到和理解的事件上,代价是无视像生态和气候紊乱那样无法言喻的影响。
然后还有正常化偏见(normalcy bias),它使我们无法相信我们之前从未经历过的灾难,从而低估或无法做出应对那些灾难的计划。基线转移综合症(shifting-baseline syndrome)则意味着“我们所知的世界”可能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变得越来越糟。
“不注意视盲”(inattentional blindness)现象使我们在专注其他事情(比如,我们是否有能力养家糊口)的时候,注意不到哪怕是最明显的重大事件。在典型的选择性注意实验中,受试者在经过一群篮球运动员的时候总是注意不到旁边有一个穿成大猩猩摸样的人在悠闲地跳舞。
变化视盲(change blindness)指人在注意力中断后注意不到环境的变化,比如在开车时看短信。“对变化视盲的视盲”(change blindness blindness)则进一步加重了这种视盲:我们拒绝相信自己可能忽略了如此显著的事情。
这个单子还可以一直列下去。距离偏见、相似性偏见和“同情心消退”使我们倾向于无视他人的困境。生活质量或生活方式攀升促使大多数有能力消费的人消费得更多而不是更少,也使我们极其抗拒放弃英国人所说的“现代便利”(mod cons);就像麦克基本在他的书《自然的终结》(The End of Nature)中说的那样,“我们不是不能自愿简化生活方式,我们很可能是不想那么干”。
我们的演化使我们准备好应对某些威胁,而在面对在这之外的威胁时,我们人类物种大脑倾向于创造出感知扭曲,以上只是其中的一些。这些感知扭曲使我们无法采取希望者(hopers)劝说我们采取的很多行动。鼓吹希望的环保主义作家真的相信我们作为人类是动物王国的成员、有生世界的一部分吗?还是说,他们实际上赋予我们某种特别的物种地位——而从一开始使我们陷入了麻烦正是这同一种(认为人类这个物种地位特殊的)人类中心信念?
对有效政府政策的希望,也同样不切实际。政府也受法律约束。在这场关于火腿和鸡蛋的讨论中,政府扮演的是“猪”的角色——为项目献身直至死亡,而我们其余人则只是“鸡”。正如霍默-迪克森所指出,政府陷入了“足够还是可行”(enough vs. feasible)的两难境地:他们可能采取的足以避免灾难的行动往往不可行,而可行的行动却不足以解决问题。
由于民主政府本质上是按短期选举周期来运作的,故而,任何胆敢制定长期环保政策的政府,可能除了加速自己的政治死亡之外,几乎无法实现太多成就。在很多情况下,在环境问题上表现出勇气的政府只会在接下来的选举中,把反环境的专制者送上台。
虽然存在诸多逻辑和后勤问题,希望修辞依然不仅继续存在,而且仍然是受保护的主流演说模式。这种修辞不受质疑和审视——就像古道尔说的那样,“没有希望,一切就都完了”。
可真是这样吗?抑或,这种说法实际上戏剧性地反转了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历史中充满了无望的斗争。甚至很多在世的人,在说到下战壕的理由的时候,也不会想到希望——事实上,他们无法承受这样的情感。大多数人上战场,是因为他们必须去。其他人则会谈到荣誉和义务、对家国的热爱、对更高事业的忠诚、考验自己毅力的冲动,或只是想让他们知道的世界继续存在下去。那种认为我们需要希望才能继续前进的论调,对那些不顾希望继续前进的人的牺牲不公,也低估了我们所能成为的一切。
有关气候变化中希望和行动之间因果关系的科学研究很少,表明这一问题难以研究。例如,心理学家玛利亚·奥加拉(Maria Ojala)2023年对气候变化时代希望起到的作用的研究综述发现,对希望的不同定义导致了矛盾或不确定的结果。她考察的一些研究表明,建设性的希望与人们参与运动呈正相关,但基于气候否认的希望则与人们参与呈负相关。
在实际情境中,这种现象随处可见。随着越来越多无可辩驳的证据被公开传播,那种认为还有希望、还有时间的说法,反而将一些人进一步推向否认,另一些人则陷入更深的认知失调状态——这两种心理状态都会造成巨大的情感和精力成本,加剧了我们总体的瘫痪状态。
“长久失败”的大智慧
公平地说,目前还没有人能成功激励那些麻木的大众(包括所谓的“警钟派”和“末日论者”)。就像科佩基所言,吓唬人和不吓唬人都不起作用——如果“起作用”的意思是,让他们有办法在心理上应对灾难势不可挡的临近,并帮助他们摆脱由此而产生的瘫痪状态的话。
这对任何论证模式来说都不容易。华莱士-威尔斯评论说,对这样一场气候变化灾难——它造成的生命损失已经约等于“一年搞一次大屠杀”,并且,在气温升高2度的情况下,到本世纪末,仅空气污染就可能杀死25次大屠杀才能杀死的人——来说,“除神话和神学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类比”。
所以,为什么不诉诸神话呢?我们是要把英雄故事情节留到别的什么地方用吗?托尔金的长久失败近在眼前,经过六十多年的锤炼,对我们的时代来说,它就是奇迹般的契合之作。修辞家们不愿意接过这个工具,无论是因为学院左翼的“智熄”(intellectual hypoxia)还是因为某种跨学科的“树冠避羞”(crown shyness),我们都不能再忽视托尔金的这个礼物了。
由于种种原因,希望修辞在这种情况下失败了,长久失败却成功了。它尤其适用于我们当前多时间线的斗争,因为托尔金笔下的精灵是永生的,他们因此能够从生态和进化的时间尺度来看历史。这使他们能够理解,甚至魔戒圣战的伟大胜利,也只是在长久失败中的短暂喘息。
这种真正长期的观点具备多重价值,其中之一是能够立即提供心理上的解脱。将历史视为连续的而非片段组成的,重新组合了时间——拉伸过去以减轻我们当下的负担——使时间足够地“渐进”,如此,未来看起来就几乎是可以掌控的了。
托尔金的这一构想只能说是准确,并不算什么先见之明。那些关注我们行星地球总体发展轨迹的人,只要不擅自把个体环境的成功说成是有意义的系统性胜利,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长久失败就是对现实的简单描述。
事实上,很多人认识到了这点:许多人和托尔金一样,把历史描绘为一条下行曲线。基督徒把我们的衰落追溯至人的堕落,而许多历史学家又把人的堕落追溯到基督教的兴起。作家罗纳德·赖特(Ronald Wright)谈到了“进步陷阱”(progress traps)——技术创新使文明能够在一场螺旋式上升的追赶游戏中,发展到需要更多创新的程度,这场游戏会一直持续,直到文明崩溃。
开创性的生物学家E. O. 威尔森(E. O. Wilson)甚至更进一步,提出了他所谓的“演化自催化”:一种自身引起的对变化的加速,每一个变化都会加到现有的变化之上,从而通过某种演化的复合效应,提高新变化形成的速率。
对人来说,自催化在我们物种认同和我们的异化状态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我们开始在陆地上生活并直立行走,把双手解放出来,这样才能够创造和使用工具。这一点,加上我们的社会性,使我们能够集体狩猎,从而成功捕猎比自己更大的猎物。不久之后,我们成为平原上的主导掠食者,悬于世界其他部分之上的不稳定位置,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束缚,却依然要依赖自然的储藏。持续的自催化进一步加剧了我们与自然的疏离;随后的发展,如文明的兴起、农业的出现、工业资本主义和犹太—基督教的传播,又多重强化了这个疏离。
这些关于人类堕落状态的变体,和托尔金的长久失败讲述的故事大致相同,但有一个关键区别:它们不是故事。更确切地说,犹太—基督教是故事,也是最伟大的故事之一——但它属于另一方,即属于物种例外论版(species-exceptionalist version)的人类,后者支持自然世界的去神圣化。
然而,我们最初也是最关键的谋生工具之一——故事,正是现在我们需要的东西。人脑演化到会被故事吸引并记住故事的程度,就是为了让知识(“山那边有狮子”)塑造行动(“让我们换条路”)。我们远古祖先对故事的本能反应,可能能够冲破那些导致我们瘫痪、相对较新的演化特征。
在很大程度上说,正是华莱士-威尔斯《不宜居的地球》中的叙事和生动想象使公众对灾难有了迫在眉睫的意识。用数据和说教来对抗故事,甚或用轶事来对抗史诗,只会让世界人民僵滞、乌合,并最终将我们引向一个短暂且彻底的失败。
将自己置身于长久失败的故事中来想象,会为我们的故事重新注入诗意和力量。这种视角向我们表明,一切个人的牺牲和英雄主义行为都是我们旅程的一部分。如果运用得当,这种长久失败修辞能激励人们参加拯救物种和栖息地的战斗,尽其所能减缓气候变化。
它还能提醒我们,即便在无望情况下,我们也有很多办法应对失败的前景和失败的现实。我们真正的物种优越性,就存在于引发我们灾难的物种傲慢(species arrogation),和如今在应对灾难时产生的物种羞耻(species shame)这两极之间,那里有的既不是希望也不是绝望,而是勇气、英勇、幽默和爱;是一种自我牺牲和坚韧的能力;是人与人的情谊和自我的深化;是转变,在一些情况下也是信念。与等待希望来引发奇迹般的巨变相反,我们可以用长久失败的故事尽力顺势而为。
我们是失败连续体的一部分——我们有人作伴,而不是在历史中孤立无援,独自面对包含不可能任务、要求无法实现的胜利的大块时间——这样的想法也能给人安慰。长久失败表明,情况一直如此,承受过去的结果并非新鲜事,我们的困境也非独一无二。
我们并非孤立无援,也不是第一个在开始之前就失败的,尽管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个。就像魔戒圣战中领袖对一位惊恐气馁的同伴说的,所有活着看到这样的时代的人都希望自己没看到,可“这不是他们能决定的。我们唯一需要决定的,是如何使用给予我们的时间”。
在这个故事中,失败带有重要的限定条件。首先,它是长久失败,这就提醒我们,虽然情况可能无可挽回,但还没到无力挽回的那一步。仍然有希望——不过是另一种希望,是对微小胜利和勇敢战斗的希望。其次,我们被召唤去“与长久失败斗争”,而不是躺下任其蹂躏。
我们需要这种对英雄主义的呼唤,希望修辞中严重缺失的就是这种呼唤。谁会愿意在无法得到认可甚或是荣耀的情况下与黑暗势力斗争——哪怕以微不足道的方式?谁又会想在明知牺牲是理所当然的情况下作出牺牲?
托尔金笔下的希优顿国王在圣盔谷之战中寡不敌众、面临必败结局时说的话展示了长久失败的心态:“末日将不再遥远。但我不会坐以待毙,像落入陷阱的老獾一样束手就擒。我要策马向前……也许我们会杀出一条血路,或打出个值得歌颂的结局——如果以后还有人为我们歌唱的话。”
对故事讲述者的呼唤
回想起来,让人觉得奇怪的是,有那么多的作家和思想家认为接受末日论会导致认命般的不作为。这其实不是我们人类的真实经历。当我们所爱的人被诊断出绝症的时候,我们并不会一走了之,或坐在那里无所作为。
事实上,心理咨询师、神职人员和医疗专业人士倾向于认为,面对终末会唤起人性中最好的一面。面对死亡的人经常会“找到自己的勇气”,就像托尔金在描绘一名怯战角色时写到的那样。他们会为自己的死寻找意义,会焕发出自己从未意识到的内在力量。爱他们的人,则可能首次见证人性中的光辉。
我们正在进行最后的斗争,承认这一点,我们便可以把人类那种连接、爱和同情的能力用于积极的目的——这是我们物种优势的一部分,它使我们得以主宰整个行星地球。很多人感受到的悲痛和恐惧,会因此而得到智慧和成熟的补偿。
矛盾的是,接受我们正面临注定失败的事实,也将是朝实现科利尔长远希望所需的精神和本体论改革迈出的第一步。它体现了一种物种谦虚,此乃原住民世界观的核心元素之一。与古道尔那样的希望派继续依赖所谓的“不屈的人类精神”不同;接受我们可能输掉这场斗争甚至被消灭,就是承认我们事实上很容易被征服。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完全重新融入自然的其他部分(除非被迫如此),但接受我们作为物种的局限性,可以开始拉低存在巨链(Great Chain of Being)的高度,直到我们能够触碰到生命之网的边缘。
显然,迄今为止,人们关于气候危机和生物多样性危机的信息传递完全失败了。那些收集和传递数据的人似乎为此感到困惑。2024年5月,当《卫报》采访了380位顶尖气候科学家,询问他们关于未来的看法,得到的回应是夹杂着困惑的沮丧情绪。
一位科学家说,“我发现形势让人愤怒、痛苦、不知所措”。另一位回答说,“世人对数据的回应应该受到谴责——我们生活在一个傻瓜的时代”。第三位科学家在描述最近ICCP报告的作者时,说他们已是“强弩之末”。
关于世界现状和我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的故事被讲述得如此拙劣,对此,我们不该感到奇怪。作为科学家的主要抄写员,活动家和学者依然执着与传递希望的信息,但这样的信息正日益成为不诚实和懦弱的信息。他们不能理解激励人心的东西和令人沮丧的东西之间的区别,因此,他们不适合讲述即便是关于最好的时代的故事;更遑论为如此紧迫的当下打造一种有效修辞。
如果他们继续拒绝面对真相的荆棘,我们将需要尽快转向那些有勇气直面现实的故事讲述者。我们需要聆听那些理解我们当下任务的人:通过与摧毁天地的力量进行长久失败的斗争来延迟结局。在这个延迟中,我们或许可以创造一个值得铭记的结局,哪怕它无法挽救人类物种,却能为我们带来某种救赎。
译者:王立秋,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